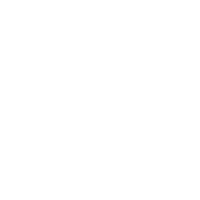杜甫《咏怀古迹-群山万壑赴荆门》
《咏怀古迹·群山万壑赴荆门》出自唐诗三百首全集,其作者为唐朝文学家杜甫。古诗全文如下: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
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
【前言】
《咏怀古迹五首·其三》是唐代伟大诗人杜甫于唐代宗大历元年(766年)在夔州(治今重庆奉节)写成的组诗。这五首诗分别吟咏了庾信、宋玉、王昭君、刘备、诸葛亮等人在三峡一带留下的古迹,赞颂了五位历史人物的文章学问、心性品德、伟绩功勋,并对这些历史人物凄凉的身世、壮志未酬的人生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并寄寓了自己仕途失意、颠沛流离的身世之感,抒发了自身的理想、感慨和悲哀。组诗语言凝练,气势浑厚,意境深远。
【注释】
⑼明妃:指王昭君。
⑽去:离开。朔漠:北方大沙漠。
⑾省:曾经。
⑿环佩:妇女戴的装饰物。佩:通“佩”。
【翻译】
千山万岭好像波涛奔赴荆门,王昭君生长的乡村至今留存。从紫台一去直通向塞外沙漠,荒郊上独留的青坟对着黄昏。只依凭画图识别昭君的容颜,月夜里环佩叮当是昭君归魂。千载琵琶一直弹奏胡地音调,曲中抒发的分明的昭君怨恨。
【赏析】
第三首是杜甫经过昭君村时所作的咏史诗。想到昭君生于名邦,殁于塞外,去国之怨,难以言表。因此,主题落在“怨恨”二字,“一去”二字,是怨的开始,“独留”两字,是怨的终结。作者既同情昭君,也感慨自身。这第三首,诗人借咏昭君村、怀念王昭君来抒写自己的怀抱。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诗的发端两句,首先点出昭君村所在的地方。据《一统志》说:“昭君村,在荆州府归州东北四十里。”其地址,即在今湖北秭归县的香溪。杜甫写这首诗的时候,正住在夔州白帝城。这是三峡西头,地势较高。他站在白帝城高处,东望三峡东口外的荆门山及其附近的昭君村。远隔数百里,本来是望不到的,但他发挥想象力,由近及远,构想出群山万壑随着险急的江流,奔赴荆门山的雄奇壮丽的图景。他就以这个图景作为此诗的首句,起势很不平凡。杜甫写三峡江流有“众水会涪万,瞿塘争一门”(《长江二首》)的警句,用一个“争”字,突出了三峡水势之惊险。这里则用一个“赴”字突出了三峡山势的雄奇生动。这可说是一个有趣的对照。但是,诗的下一句,却落到一个小小的昭君村上,颇有点出人意外,因引起评论家一些不同的议论。明人胡震亨评注的《杜诗通》就说:“群山万壑赴荆门,当似生长英雄起句,此未为合作。”意思是这样气象雄伟的起句,只有用在生长英雄的地方才适当,用在昭君村上是不适合,不协调的。清人吴瞻泰的《杜诗提要》则又是另一种看法。他说:“发端突兀,是七律中第一等起句,谓山水逶迤,钟灵毓秀,始产一明妃。说得窈窕红颜,惊天动地。”意思是说,杜甫正是为了抬高昭君这个“窈窕红颜”,要把她写得“惊天动地”,所以才借高山大川的雄伟气象来烘托她。杨伦《杜诗镜铨》说:“从地灵说入,多少郑重。”亦与此意相接近。究竟谁是谁非,如何体会诗人的构思,须要结合全诗的主题和中心才能说明白,所以留到后面再说。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前两句写昭君村,这两句才写到昭君本人。诗人只用这样简短而雄浑有力的两句诗,就写尽了昭君一生的悲剧。从这两句诗的构思和词语说,杜甫大概是借用了南朝江淹《恨赋》里的话:“明妃去时,仰天太息。紫台稍远,关山无极。望君王兮何期,终芜绝兮异域。”但是,仔细地对照一下之后,杜甫这两句诗所概括的思想内容的丰富和深刻,大大超过了江淹。清人朱瀚《杜诗解意》说:“‘连’字写出塞之景,‘向’字写思汉之心,笔下有神。”说得很对。但是,有神的并不止这两个字。只看上句的紫台和朔漠,自然就会想到离别汉宫、远嫁匈奴的昭君在万里之外,在异国殊俗的环境中,一辈子所过的生活。而下句写昭君死葬塞外,用青冢、黄昏这两个最简单而现成的词汇,尤其具有大巧若拙的艺术匠心。在日常的语言里,黄昏两字都是指时间,而在这里,它似乎更主要是指空间了,它指的是那和无边的大漠连在一起的、笼罩四野的黄昏的天幕,它是那样地大,仿佛能够吞食一切,消化一切,但是,独有一个墓草长青的青冢,它吞食不下,消化不了。想到这里,这句诗自然就给人一种天地无情、青冢有恨的无比广大而沉重之感。
“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夜月魂。”这是紧接着前两句,更进一步写昭君的身世家国之情。画图句承前第三句,环佩句承前第四句。画图句是说,由于汉元帝的昏庸,对后妃宫人们,只看图画不看人,把她们的命运完全交给画工们来摆布。省识,是略识之意。说元帝从图画里略识昭君,实际上就是根本不识昭君,所以就造成了昭君葬身塞外的悲剧。环佩句是写她怀念故国之心,永远不变,虽骨留青冢,魂灵还会在月夜回到生长她的父母之邦。
“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这是此诗的结尾,借千载作胡音的琵琶曲调,点明全诗写昭君“怨恨”的主题。据汉刘熙的《释名》说:“琵琶,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琵,引手却曰琶。”晋石崇《明君词序》说:“昔公主嫁乌孙,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尔也。”琵琶本是从胡人传入中国的乐器,经常弹奏的是胡音胡调的塞外之曲,后来许多人同情昭君,又写了《昭君怨》、《王明君》等琵琶乐曲,于是琵琶和昭君在诗歌里就密切难分了。
前面已经反复说明,昭君的“怨恨”尽管也包含着“恨帝始不见遇”的“怨思”,但更主要的,还是一个远嫁异域的女子永远怀念乡土,怀念故土的怨恨忧思,它是千百年中世代积累和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乡土和祖国的最深厚的共同的感情。
话又回到此诗开头两句上了。胡震亨说“群山万壑赴荆门”的诗句只能用于“生长英雄”的地方,用在“生长明妃”的小村子就不适当,正是因为他只从哀叹红颜薄命之类的狭隘感情来理解昭君,没有体会昭君怨恨之情的分量。吴瞻泰意识到杜甫要把昭君写得“惊天动地”,杨伦体会到杜甫下笔“郑重”的态度,但也未把昭君何以能“惊天动地”,何以值得“郑重”的道理说透。昭君虽然是一个女子,但她身行万里,冢留千秋,心与祖国同在,名随诗乐长存,是值得用“群山万壑赴荆门”这样壮丽的诗句来郑重地写的。
杜甫的诗题叫《咏怀古迹》,说明他在写昭君的怨恨之情时,是寄托了自己的身世家国之情。他当时正“飘泊西南天地间”,远离故乡,处境和昭君相似。虽然他在夔州,距故乡洛阳偃师一带不象昭君出塞那样远隔万里,但是“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洛阳对他来说,仍然是可望不可即的地方。他寓居在昭君的故乡,正好借昭君当年相念故土、夜月魂归的形象,寄托自己想念故乡的心情。
清人李子德说:“只叙明妃,始终无一语涉议论,而意无不包。后来诸家,总不能及。”这个评语的确说出了这首诗最重要的艺术特色,它自始至终,全从形象落笔,不着半句抽象的议论,而“独留青冢向黄昏”、“环佩空归月夜魂”的昭君的悲剧形象,却在读者的心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起句突兀奇绝,不同凡响:三峡之水从千山万壑间流过,山势峥嵘起伏,有如万马奔腾,直赴荆门。江之北岸传说依旧坐落着昭君村。上半联如高鸟俯瞰,境界宏远;下半联则似电影中的“定格”,具体点明古迹所在,很自然地将昭君的故事安置在“高江急峡”的阔大背景中。一个“赴”字,画龙点睛,使山水充满了生机;一个“尚”字,写出江村古落依然如故的状态。大小映衬,动静相间,不仅使画面显得生动,同时使诗的意境更深一层。因为“尚有村”传达了一种“斯人已去”的寂寞感;自然界无穷的生命力,更加重了“物在人亡”的惆怅情绪,巧妙地为全诗确定了悲壮的基调。陡起直转,必然过渡到下面对昭君命运的咏叹。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颔联概括了昭君一生的悲剧。据《汉书·匈奴传》记载:汉元帝竟宁元年(前33),“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一去紫台”便说此事。“紫台”即紫宫,天子居处;“朔漠”指匈奴所在之地。“青冢”即昭君墓,在今内蒙古境内。据《归州图经》记载:“边地多白草,昭君冢独青。”这两句以极简的文字,写出了无穷的感慨,写出了昭君生前死后的哀怨。
清人袁枚论诗曰:“诗如鼓琴,声声见心。”(《续诗品·斋心》)杜甫以“紫台”对“青冢”,一雍荣华贵,一凄凉冷清,在色调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以“朔漠”对“黄昏”,又烘托出一种肃杀渺茫的凄惨气氛。先从字缝中透出了强烈的悲剧色彩。“连”、“向”二字,更是颇具匠心,前者将“紫台”、“朔漠”连在一起,无形中就把昭君出塞的悲剧和西汉朝廷的昏庸联系了起来;后者使同种色调互相渲染:青冢瑟瑟,面向暮霭沉沉,一片萧条充塞广宇,象征着“此恨绵绵无绝期”。从而给人留下了丰富的联想余地。这两句中的“朔漠”、“黄昏”,又是叠韵双声。这正如《贞一斋诗说》所云:“音节一道,难以言传,有略可成为指示者,亦得因类悟入。如杜律‘群山万壑赴荆门’,使用千山万壑,便不入调,此轻重清浊法也。”可见杜甫确实是“语不惊人死不休”。
“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夜月魂。”杜甫此联虽然紧承上联之意说出,但却由咏古迹转向了咏怀与议论,揭示了造成昭君悲剧的原因。“画图省识”句,本于《西京杂记》的记载:“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按图召幸。宫人皆贿画工,昭君自恃容貌,独不肯与,工人乃丑图之,遂不得见。后匈奴入朝,求美人。上案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帝悔之,而重信于外国,故不复更人。乃穷案其事,画工毛延寿弃市。”对这一句的解释,历来有分歧,或曰:假使汉元帝能从画图察识昭君的美貌,就不会有魂魄空归的遗恨了;或曰:昭君已一去不返,后人只能从画图上去辨识她的丰姿了。这都不符合杜甫的本意。根据律诗对仗法则,“省识”对“空归”,“空归”既为偏正词组,“省”字就该修饰“识”字。朱鹤龄认为:“画图之面,本非真容,不曰不识,而曰省识,盖婉词。”(《杜诗详注》引语);浦起龙也说:“‘省识’只在画图,正谓不‘省’也。”(《读杜心解》)。这才是准确的理解,才符合杜甫咏昭君的根本动机。实际上这两句诗具有内在的因果关系:正因为汉元帝昏庸,“按图召幸”,使小人有机可乘,故而辨识不出美恶真相,才害得昭君遗恨终身。这就把帐算在了昏君、佞臣的头上,含意深广。杜甫自己“窃比稷契”,结果却遭到君王的厌弃,终老江湖。因此,他对昭君的厄运充满了同情,对昭君的故国之思有着充分的理解。然而他深知奇冤已经铸就,纵使昭君魄魂归来也是枉然了。“空归”二字真写得肝肠寸断,把万千遗恨表达了出来。“春风面”与“夜月魂”更是对得惊警:昔如彼,今如此,讽情贬意隐于色彩不同的六字之中。
“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相传“昭君在匈奴,恨帝始不见遇,乃做怨思之歌”。(《琴操》)此联写得真切率直,说的是千载之下,人们分明能从昭君演奏的琵琶曲中,听到她那无穷的怨恨。
白居易论诗要“卒章显其志”(《新乐府》序),杜甫却说诗要“篇终接混茫”(《寄彭州高适岑参三十韵》)。乍看二语抵牾,而事实上当诗歌“显其志”时,诗思也就达到了高峰。这是诗人对所叙之事的一个总结,又是诗人感情最强烈的抒发,而此时此刻最能发人深醒,这也就是“篇终接混茫”。杜甫在写了昭君的悲剧以及悲剧的根源之后,毫不隐讳地以怨恨作为一诗归宿,正是“卒章显其志”。仅就昭君命运来看,她“一去紫台”,便“独留青冢”;因“画图省识”,而“环佩空归”,怎能不怨呢?她要怨生前不见遇,怨死后的无依,怨君王昏庸,怨小人险诈。茫茫六合有多大,她就有多少哀伤,那琵琶曲中就有她多少怨恨!不过,“看杜诗如看一处大山水,读杜律如读一篇长古文”(黄生《杜诗说》),七律作者是把“一腔血悃”凝铸在五十六字之中,字字精深、不可轻议。这首诗题为“咏怀古迹”,重心是在咏怀上。如果只以昭君之怨作结,只能算是咏史。这不仅理解不到杜甫的情怀,还会产生误解。以前吴若本、《读杜心解》等误把这组诗分为咏怀一章,古迹四首,就是例子。其实只要结合杜甫做诗时的境况和他在政治上的遭遇来看,就绝不会得出这种结论。因为他借古抒怀的动机很明显,五首诗的联系也很密切。他在政治上的挫折,使他深感君臣际会之难;漂泊西南、依人为生的岁月使他痛苦不堪。而中原扰乱他又欲归不得。所以他咏庾信,寄托自己的乡关之思;咏宋玉,慨叹自己的怀才不遇;咏昭君,谴责君王的美恶不分;咏刘备、孔明,仰慕他们君臣无间的关系。他是借古人酒杯浇自己胸中的块垒。那么可见,这曲中倾诉的怨旷之思岂止属于昭君一人,它分明也是杜甫的怨恨;而不辨美恶的君主又岂止是汉元帝一人,后来有多少人才仍在抒发着感世不遇的情怀!这一曲怨恨已流传千载,谁又能断言它不再继续下去?这一结,切中时弊、含意深远,正是“篇终接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