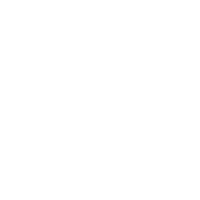【短篇小说】金色房子
天已经亮了,紧闭栓锁的窗扇和杏黄色的百叶窗帘通透单薄,上午的天光告密般爆裂而入。观察室狭小而独立,窗口的窄轮廓在一侧平整的黄色墙面上映成灰色的碑。在那片阴影之下出现的薄薄人形,透满了模糊的黄色微光。我试图描述这种在日悬之时一再上演的颜色,规律循环,了无终结,填充着空间,如一张难过的脸。我站在门口,鼻翼下深深吐出好大一团气----我深夜出逃的小犯人就坐在那。
她换上了白色的棉制服,和这里的其他人一样,显得苍白安静如白瓷瓶中断绝光线的植物。那双眼睛依旧如同被掏空的洞穴,她的视力是什么时候坏掉的?来这之前?一只眼睛只能看见模糊的轮廓,是哪只眼瞳来着?从外面看不出来。从外面看不出来的东西太多了。
我叫她,落儿。她坐在床边拉耸着双腿,看见我,她想从床上站起来,然后突然就弯下腰吐了。
“你又去找埃狄亚了,是不是这样?”
她不答话。我把右拳狠狠砸进左边手掌里,差点原地打个转。我就知道。窗台上有别人送来的水仙花。大家不约而同,一下子送来了好几盆。那饱满如女孩身体的花朵根部绽开深而整齐的伤口,乳白色的汁液从中汩汩流淌而出。我跟落儿说过,别干这样的事,刀子必须没收,连同在她锁骨间摇晃的菱形项坠,一切锋利的东西。“交给我。”我对她说,“找地方给你保管。”但是花茎上的伤口依旧时不时出现,规整如受到了见习期女巫认真又精确的诅咒,左边、第五株、伤口三道纵列、一种可怕而无止境的重复。
“是猫吧。”落儿说。若无其事。可未免也实在太若无其事了。
讳莫如深。我向窗外望去,那被污蔑栽赃的幽微生灵正卷着漆黑细瘦的尾巴在杂草丛生的花坛上巡走。出于人眼所能感知之物极为有限的可悲考量,人所不可直视的部分----这座半监禁式处所中的最大仇敌----竟径直交由园中逡巡的四只黑猫守卫戒备。不过不得不说这些个玩意也诚然是不讨喜,时常预兆全无地咧嘴怪叫,脊背弓弯如同胀裂,四肢直挺地从某处毫无由来地跳开,碧眼如迸,在人的尖叫声中一头飞进门口小护士怀抱中装得满满的洗衣桶里。
“反正你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努力克制着说。
“是猫。猫抓水仙。”落儿重复了一次,声音脆而飘,带着一种仿佛能滴下水来的永恒悲哀。“一只猫跳进滚筒洗衣机里死了。那些畜生发了疯。整夜像小孩一样哭叫。”
罢、罢。我生生无法再问下去。因为落儿皱着眼眉,带有一种微微痛苦的神情,弓着身子又回到床上去了,日子里的绝大部分事情都可以被她的虚弱和无辜苟且摆平----说实话,我可真是不太喜欢她这一点。
花盆里有些泥土,我把它从窗台上取下,混杂着死去的水仙花的根系,将落儿吐在地板上的东西收拾干净,倒好了水哄她漱口。长发在她低头时垂下,没有菱形项链遮挡,喉间心形的伤口鲜活可见。
“我们不是已经念过祷,什么都说好了吗?”我用手抚着她薄薄的背,“以前的事情,再也没有办法,但往后的事既然已经说好,就该按说的做。”
她不答话。微张的口中露出清晰的小尖牙齿。
“为什么还是要去找埃狄亚呢?”我忍无可忍。
“是他直接撞见了我。”
“他也许就是来找你的你懂吗!他就是来找你的!为什么不能视而不见呢?”
“做不到!”
她抬起头来,惊惶无措地看着我,凝滞几秒,像是词汇在脑海中飞快亡佚、无法捕捉一样,然后突然便吼出声来。情感满溢而起伏。壅塞中的小小身体发出濒临爆炸般的颤抖。眼泪是唯一的出口,顺着她尚未出落立整的脸庞轮廓蜿蜒而下。咸涩的浸泡里,喉间的伤口殷红如初----罢、罢。我真是根本不知道该说她什么好了。
她哭了一会,稍微平静了些。我想着要不要给院长报个信,不用找了,落儿回来了。怎么回来的?当然是自己乖乖跑回来的。做完了世界上的头等大事就跑回来了呗。结果根本就没人找她,呐,干脆就没人知道她跑了。省了我一番口舌,不然我怎么说?我跟你说----我都没法跟你说----唉。时至今日,我用指甲盖都能想出来在昨天落儿失踪的晚上两个人又搞了些什么名堂。我面前抽泣不止的女孩惊惧但欢快地跑了过去----我都能想象到她跑的时候额前的头发一飞一舞的样子----埃狄亚的拥抱如张开的大网般笼罩在她细小的身上,手臂间时而过于强劲的力道中传来她短促的惊吟。然后呢?然后还能有什么花样把戏?!修长优美的手掌如执明珠一般捧起了我面前的这张苍白的小脸,尖而锋利的牙齿深深吻向裸露的喉间。咕咕咚----喉结跳舞,他咽下她的血。
“是怎么啦?这里?”
一名老账房负责看护照顾她,确保她不会到处乱跑。啧啧,不会到处乱跑。啧啧啧啧。气得我简直想朝他咋烂舌头。没办法,人手不够。“爱德华区”的人们太会背地里找麻烦,明眼人都弃岗迁离、另谋高就。观察室完全落入那些个老不死又挪不动的人之手。当然钢铁护卫者也有之,但都被毫不浪费地放置在那些个刀刃上。从镖局花重金雇来的年轻力壮的男护士,通通送进对面的“狼人区”。那边的戏份比这里足多哩,踢打撕咬、丁零当啷、桌椅板凳、锅碗瓢盆----为高贵优雅的“爱德华区”所深深不齿。在这里,一切关注都缘于防备。落儿深谙此道,成为她用弱小又无辜解决看守问题的一大典范之举:她就在床上坐着,瞪着大眼睛,偶尔自己和自己玩一些个可怜兮兮的扑克游戏,吃烤曲奇都小口小口地从不发出声音,乖得就像被拔了电源而停下来的舞蹈娃娃。所以呢?就让这小孩跟老掉牙的账房相依为命去吧!可真会省事啊。
老账房走进来。一边臂膀的袖子挽着,支起的脖颈缩进高耸又弯曲的肩胛骨里,让人想起动画片中一种尖嘴巨喙的鸟类。
“有趣得很啊落儿,当真不想去转转?有编织、手鼓、刺绣、菠萝饭和人体彩绘!”老头说着,向我们展示他晾起的手臂,上面棕色和黄色的圆形花纹在老年斑的空隙中艰难地延伸着。“现场教学哦,印第安人的彩绘课连我都想去旁听咧!”
我向窗外看了看,他说的是正门前广场上的周末集市。一个个红顶帐子支起的小摊位像蘑菇一样耸着,虎虎生气。我看了一眼落儿,她双手环抱,摇了摇头。
“落儿不大舒服。”我说。“早上的秋葵粥可还有?”
老头站在原地,等候答复的眼睛在松垮垮的眼眶中转来转去,恨不得转到地上----就是这种耳背的、脑子里有锈的老家伙。
“早上的秋葵粥。”落儿重复道,“有没有,还?”
“早上?”老头大为不解,“可是这都快十一点了呀!上哪找‘早上的秋葵粥’去?早上?”
我大翻白眼,拿这种人你还能如何?于是老头见没什么事,便走出房间,又欢天喜地地到别处展示他手臂上的怪异彩绘去了。
“他真的是账房吗?”我无比愤慨地说,“我觉着他比这的大部分人都不正常。”
落儿“扑哧哧”笑起来。看她一笑,我一早晨的气消了一半。
“哎,多么快乐的老头的一天啊。”落儿收了笑,突然轻声感叹道。
“你也能这样快乐呀,”我凑到落儿的床上,热热络络地说,“只要你……”
“你又来了!知道你要说什么!”
“不不不!”我摆手道,“绝没有说‘只要你忘掉埃狄亚’那种话,是让你们都好好的,但绝对不是你们现在这做法。”
她在床上缩成了一团,看着我,眼中充满了令人悲哀的警戒和防备。
“我说,在你……也是‘那东西’的时候,你和埃狄亚是不是很开心?撇开什么他怀疑你是你怀疑他是这种相互试探的劳什子,就说相互了然之后,你们是不是有真的很开心的时候?”
“什么叫‘那东西’呀?”
“你呀你,你明明知道的呀。”
“可我不想让你们这样叫。我们已经为这事受了好多罪了,说一说都觉得羞耻?”
“没有没有,没有羞耻呀。”我赶紧说,“在你也是……‘爱德华’的时候?天下着大雪,一踩上去便发出吱吱的声响时,你们两个在谁也不知道的角落里,偷偷分享珍贵的无辜小动物的血的时候,是不是温暖又开心的?就说有没有这样时候?”
“----有的。”
“呐。你在学校念书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可连我都不告诉----知道自己的同类就在身边,原本孤寂得不行的日子,是不是一下子就得到了无可替代的安慰?就说有没有这样时候?”
“----啊……有的。”她低眉,偷笑起来。我真想看她笑。
“我说----你们在图书馆私会的日子不少吧?一转身想叫你,人影都没有了!你到底把AB型血的小松鼠藏在哪里带进去的?你那件黄金小夹克的上衣口袋?那图书馆墙上可大字写着:“严-禁-饮-食!”
她又“扑哧哧”笑起来。
“而你是想变好的,对吗?你们不该在夜里相见,吸血鬼的体系完备又自足,和周围封得严严实实的。这根本就不是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而是从一个漩涡里挣出来。虽然你们相互取暖,但为的却是暖和着呆在那漩涡里永远也不出来。可是你是想要变好的,是不是?就说是不是这样的?”
“----算是的。”
“那事情不是明摆着的嘛!”我说,揽住她瘦瘦的肩膀。
“乖乖地在这里变好了,有我陪着,我是绝对不走的。什么也别想,不要去见他。一想起他来只能想起过去的美好回忆来,岂不美极了?喂喂我说,多么难得珍贵的经历呀!我还羡慕你咧!真的,我长这么大来所见到的大部分人,都是那种无趣又无聊的货色。”
“----唉。非这样不可?”
“你想怎样?人前被看得好好的,人后一转眼便偷偷跑出去,开喉咙,放血,‘咕咕咚’,然后连魂都不剩地跑回来,整晚不睡地把自己变成一只蝙蝠?这样?”
我看着落儿。她的眼中如同星辰坠落。
“哪只好?左眼还是右眼来着?”
她各自闭上试了一下。
“左边是好的。唉唉,右边是什么都看不清了呢。像蒲公英一样的。”
“蒲公英?”
“是的呀。好像在蒲公英里面,蒙着许许多多又小又透明的细腻绒毛。”
她转过脸来,将左眼挡住,看着我,楚楚地点了点头。
“对我们都不好,是不是?”
“早就和你说嘛。你,你就不该认得他。还什么……‘我们维持生活皮相’、‘我们谁也不告诉’,这种事情从一开始就不可能。落儿,人耐不得太过孤孑的环境,人都是靠着这种并不高明的本性得救,感到痛苦、感到无法忍受、然后人就会去寻求被理解、被接纳的生活空间,人会因为无法忍受在一个没有认同感和现实感的世界里孑孓生活,而做出使自己趋向正常的尝试,如果你和他都是独立的,你们也会这样。可你们在一起却试图战胜这种本性,制造一个彼此相信的、自给自足的情景来,从而连‘消除孤孑’的愿望都没有。”
“这样不能活下来吗?”
“可你为何要一直活在边缘里。”
说到这里,我突然犹豫起来,仿佛我描述了无法完成的事情,相悖的现实如被我砌进深墙的、爱伦坡的黑猫,在我过于狂妄的叩击中发出嘲笑。看不见的东西……人眼所能及的范围过于悲哀偏又过于自负。我宁可落儿十二根肋骨全断了,像个风筝一样被人一根根装好了放在床上,或者重病不起,那样至少她能得到她应得的照料。
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又很快地低下头去。眼神优美如鸟类从崖边坠落。
“那就不找他去了。”她说。
“嗯,今晚之前决不食言?”
“当真的呀!我。想通了就不去了。不管他怎么叫我都不去了的。非得哭天抢地说的话你才信呀?”
我们在床上对坐,她的灵巧双手一张张排列着漂亮的纸牌。我们用她独创的仪式决定出牌先后,看谁抽到代表守卫者的红桃J,谁便掷出第一张牌。她经常一人分饰两角,以便这纸牌游戏能够随时进行。
“除了解牌之外,平时也做别的?”
“看书呀。你拿给我的书都看完了,还做了摘记。”
“这么认真?不赖嘛。”
“也记手账。好事就记。不天天记。”
“好呀。”
“有时也和账房老爷子聊天。”
“跟那家伙有什么说的?”
“各种事情呀。都是些没用的,但好歹也是在和人说话嘛。他不防备我,即使是望月之后,你知道的,就是……我们最危险的时候,他也不防备我。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咬伤了他,他还对我说,莫负担太重了,他没妻没儿的,混账老风湿又好不了,什么挂念都没有。他就这么说的,‘混账老风湿’。”
落儿说着,又像怕人误解似的,紧接着解释道:
“啊啊,也不是说我因此就盯上他。才不是的。一点都不是。我就是……挺轻松的。只有跟他说话才觉得挺轻松的。”
“我知道。”我说。“你已经好久不发作了吧?”
“嗯。冬天那会嘴唇裂了流血,我还用舌头舔了,那种时候真的好难撑过去啊,就像五脏在大火里打着结地烧,被烧焦了一样,哪还记得住什么什么的许多理智,满脑子想得就是迎着火苗浇下去,有多少来多少,赶紧浇灭了它。后来你猜我怎样?”她指了指窗台上的水仙花,“我把墙皮混进土里吞掉,谁都没有伤到,也没有自己放血,就根本没用得着吸血。为这事我骄傲了一周!”
“不赖呀,你!”我从后面揉摸着她微昂的脑袋,长发又凉又顺。“要坚持住啊。”
“那是当然。”
“不过这墙皮就土,未免也太恐怖了点。我下次来给你带一罐糖,你试一试,当然,平时的时候也可以吃。”
她点点头,忽然不再说话,怅然若失。我张望过去,她的眼瞳漆黑无底,下面缀绣着饱满泪滴。
“怎么了?”
“我骄傲一周的时候本想告诉埃狄亚来着。”她小声说,“本想跟他炫耀一下来着。你说他怎样说?他肯定也和我说‘不赖呀,你!’”
我轻轻叹息。
“那后来怎么没有告诉呢?”
“不能说。多么想说也不能说。有好多犹豫和顾忌,犹豫比想告诉他的冲动多得多得多,然后就把这种想法淹没了。自从我来这里之后,我们的关系变得脆弱极了,就像那种眼看都要爆破了却还在灌气的气球,可是偏偏又不破的那种,就那么不安,就那么不安。好像所有的事情都不能提一样,一提就总会变成刺激,我们不能相互变好,却只能相互感染。变成‘嘭’的一声,搞得乱七八糟,心力交瘁。”
“你和埃狄亚一直有联系啊?”
“……”
“或者是别的方式联系?”
“唉,也不是一直联系,就是想找到的时候找得到罢了,你不要问了。我又不找他。他也不找我了的。我们昨天分开的时候就说了。你说好笑不?我们只见了一个晚上,半个晚上都在说‘我们再也别见了……我们再也别见了……’就这一句话,翻来覆去呀。”
“这不是重点。可是依旧用剩下的半个晚上吸了血。”
“别说了!都说不会了的。”
“你没有吸血就好。”
“没有吸。我没有吸,我没有他那样勇敢,从一开始就是这样。我的怯懦拦住了我,也留住了我。所以我才会觉得,认清自己的本质之后,维持生活皮相会比撕破它更为明智,也更为不易。”
她顿了顿。收起床上散落的扑克牌来,再洗一遍,在手掌间碾开,黯然苦笑。
“落儿。”
“嗯?”
“不要自己和自己玩纸牌。哪怕你找那耳背的老爷子来,也不要自己和自己玩。”
“没玩呀,我。有那么严重?”
“有的。”我认真地说,“听好了,有那么严重。自己和自己打牌,毫无目标可言。你看起来是既扮这边,又扮那边;可实际上,你既不是这边,又不是那边。你哪边都不是。你哪边也不在乎。这就变成了一个根据某种既定法则或者干脆就是你编的法则来构筑一个这边出完那边出的流程体系,输赢就是听天由命。哪边赢了你都不会期望,也不会快乐,你就把拥有的所有东西一股脑地倒进这个法则里面,任由它们加工完成之后是什么。你就觉得,‘呐,就是这样的嘛。我就知道。’你知道吗?坏逻辑如果有破绽还好,怕的就是翻来覆去都说的通,完备得不行,就把人给完全吸进去叫不出来了。你可大概知道我在说些什么?”
“知道。不玩了便是。”
“落儿。”
“怎么啦?”
“下周去逛周末集市如何?我和你去。”
“那里有什么?”
“老大爷不是说有什么刺绣编织、人体彩绘什么的嘛,你忘了他举着条胳膊到处乱窜那傻样了?”
“刺绣编织……?那有什么意思。”
“或许有鱼尾裙呀。你不是想要一条鱼尾裙吗?”
“……裙子还是等好了再说吧。”
“先买下来有什么不好……”
“现在丑。”
“……哪里丑呀?”
“就是不想穿漂亮的衣服!”
我站起来,深吸气。窗口门口度个来回。又一轮无效的对话。又一轮。
雨水侵蚀失修的屋顶一角,配以眼瞳状腐烂暗蓝的霉菌,水渍在天花板上展现出令想象力丰富的头脑隐隐不安的随意样子。不要漏雨才是正事,我思量着,或许我得把这事告诉老账房,用我那一副刁蛮样敦促那没眼力见的老账房找人来给落儿修好,这事落儿是肯定不会开口说的,我知道。
小餐车的左边轮子吱呀吱呀响,老头支着他骄傲的臂膀推车而来。我回头看,打了个响指----
“来啦!吃饭了落儿。菠萝饭和三色玉米粒。看起来不错呀落儿。”
她吃玉米粒。味蕾专注地分辨。两腮有节奏地一鼓一鼓的样子像某种啮齿类的小动物。平安无事。在往后那些无可饶恕的夜里,我依旧会想起这时坐在这昏黄房间中的落儿,将灿灿的玉米粒小心地夹入口中的情形。她的人生或她的皮相人生。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称呼。时常给人前功尽弃之感。伤心之情如灭顶。她自己对这种磨人的循环遭遇却无动于衷。仿佛一切努力都只是在做梦。仿佛梦注定会醒来。醒来之后注定无处可走。从崖边坠落她也毫不悲伤。让人深深的无力。无力。她夜里双眸明亮。瞳孔会放大生光。行动灵巧敏捷如扑击捕猎。有尖齿可以划开生肉。闭着嘴巴时可以像小虎牙一样挂在外面也可以收起。不招惹人。不惹大的麻烦。但是没有任何事物,没有任何事物,能够真正触及抚慰这深陷幽深处境的她。哪怕是重重一击。也做不到。她求助扑克牌上虚幻的双头人形,在这个绝望的话语体系中越来越自然和融洽。
她回来了。从门口飘然而入。脚步在床前戛然止住,神情哀伤。脸上还留着泫然的痕迹。看不见的锋利留在窗台的水仙里,根部汁液如她颈间伤痕般娇艳明媚。它们照例死亡了。这次连晚上都等不到。太过分了。
我想我已经失望到极致。跳起来。命令落儿直视我的眼。
“你们又什么都没有做!说了一晚上‘我们不见了’然后就欢欢快快地回来睡觉了,是不是!?”
“是他找了我。”
“他发疯了!他找你!他发疯了!为什么不置之不理?”
“做不到!”
她浑身颤抖,双手插进上衣鼓胀的口袋。AB型小松鼠。我想起来。令人----虽然我不想这样说----令人厌弃的把戏。
“拿给我。”我说。
“不是的……”
“拿给我!”
“啪。”小密室般的口袋里飞出东西。她把它丢在床上。散落一片。我心疼起来,不知说什么好。因为那是一副扑克牌。
“为什么……这?”
“我们只能吸血。我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的。我们只能吸血。我们都不能进行一些寻常的游戏。直到分开的时候,都还不知道对方也把纸牌放进口袋……我一下子就哭了起来。我们甚至都没有开心地玩过任何游戏,没有打过牌,我们只能吸血,就是这样。我们是靠吸血维系起来的。我们的所有关系都是靠吸血维系起来的。”
“那为什么不玩呢?”
“那时我们已经犯下错事,各自都痛苦不已,难以承受。觉得已经不能再玩起来了。就回来了。”
“…你是说你也吸了血?”
落儿垂下头。终于呜咽起来。
“我就问你有没有吸他的血?!”
“哦我本是不想的!可是埃狄亚撕开我的喉咙,那味道太明显了!你不知道……都说了你根本就不了解……人怎么能了解……然后埃狄亚露出手腕说‘落儿你吸吧……只有我们两个……只有我们两个知道各自真正的样子……太难了,太难了呀……我们不伤害其他任何人,连小动物都不碰……好不好……谁也不要伤害……只有我们两个……好不好……我们谁也不告诉!我们谁也不告诉!’你知道吗?只有我们两个!只有我们两个!再不会有其他人了呀!”
“哼!”我气得大锤其床,“没有一个无辜!”
“不是的!”
“什么不是?”
“埃狄亚!埃狄亚也是很辛苦的呀!没有人知道他的事情,可他依旧和一群人在一起活着,像其他人一样活着!像其他人一样活着!我跟你说了你也不会明白那有多么难!一举一动都需要和自己打上好大一架!花干了气力!没有人该这么辛苦呀!”
“难道你该吗?落儿!他给你带来的是什么!别忘了你自己是怎样的!你已经被驯化,身体里流着人类的血,让你撑到这一步我好辛苦的!你想了我没有!他破坏的是我的成果!而且是你想要这样做的,是不是?等你好了,回到学校里去了,穿着漂亮裙子在学校里走啊走,在草地上撒欢打滚,玩纸牌?那纸牌还不遍地都是啊!是不是?你想想?那多好啊。我不认得埃狄亚,我不知道埃狄亚有多苦,我只认得你,我只知道你有多苦,我只知道埃狄亚找你,他吸你的血他吊你的瘾,不管你俩怎么想这件事,我们的成果分崩离析!花了好大力气辛辛苦苦抵制住的情况再度复发!”
“那不是……”
“你还要狡辩!”
她坐在床上,抽噎得好厉害,仿佛会散成碎片。她伸手。慌乱地解开衣衫领口,里面充满泪水。内在的绝望但有序的装置发条犹如失灵,偏偏在它能排上用场的时候,我走过去,轻抚她的肩。我相信她几乎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
“你以为我不怕他?不怕现在的日子?我其实害怕好多事情……是那样的怕呀……”
“到这来,落儿。你怕我吗?”
“不怕的。只不怕你。”
“那便和我呆在这。不要想他。想他救不了你,也救不了他。你对我是否放下心来?”
“放心的。只对你放心。你也不怕我?”
“不怕你,知道你会好的。不怕你。”
“是因为把我想象成好的样子才不怕我?”
“不是。不是的。你总是往坏的地方曲解人的意思。是因为觉得你好,才不怕你。”
“可那是假的……”
“你又来了,所有好的东西都是假的,只有你的小尖牙才是真的?扯哩。扯得十万八千里去了。就是因为这个你才把人都推得远远的。也许本来可以尝试的。”
“不。我再也不能承受那种负罪感了。”
“怎么是负罪感呢?”
“我咬死过猫狗。我不想伤害人的。这是必然的,这是必然的。一个人属性本身就注定要伤及周围的人,除了把自己放得远远的,还能怎样呀。”
“你把‘这是必然的’那两句去掉嘛。你这就是歇斯底里的紧张症。一针管吗啡就能治好。”
她忽然扬起头来,小兽一样的眼中流露出因看到结局而无可挽回的绝望神色。她推开我的手,在我的怀中拼命挣脱。我惊讶于她于细小身材不符的强大力道。我捉住她挥舞的手臂,依旧安抚她入怀。
“啊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呀!”
“什么来不及?我看这样做就蛮好。先把安眠剂放进糖罐子里把你放倒在床,然后我便叫医生来,给你编个好听又惹人怜惜的病,啊呀呀,说你整夜整夜难受得睡不着,像小猫一样叫,然后医生便傻呵呵地给你拿了吗啡注射进去。等我们的落儿醒过来的时候,活蹦乱跳!好的彻彻底底的。怎么样……”
她没有回答我。也不会再回答一次了。血在洁白床单上变成红莲,一滴,两滴,她张大了口,好一点也不浪费。血从我的左腕处汩汩留下,我看见她脸上泛起久违的红润光泽,眼瞳漆黑深邃如蕴藏秘密的古井,她好看的嘴角向上抽动,以一种痉挛般的频率,那是她积压已久的、前所未有过的快乐表情。
咕咕咚。咕咕咚。声音飘然远去。
咕咕咚。咕咕咚。梦境即将醒来。
笑容在她的脸上消失了。她变得像往日一样张皇无措。她看着我,血从她微张的口中溢出来,头难以置信般得轻轻摇晃,仿佛失掉了魂魄,我知道这个表情,正在成为我记忆中落儿最后的表情。神经酒醉般欢快蹦跳。鲜花漫山遍野。
“我就知道…….啊……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我苦笑着说,“我就知道你一定会说‘我就知道’……你比谁看得都清楚,所有人都傻……是不是?任何变好的尝试都是在做梦!你就等着这一天来,你好说‘我就知道’、‘我早就知道’好啦你赢了,你赢了落儿,你对你自己的原初判断赢得了事实不可辩驳的胜利…..”
“不是的!”她哭喊。“不是的!”
“不要哭了。我已经被你哭得精疲力竭。你有什么好哭的。落儿。你有什么好哭的呀?我跟你说,你也不是什么好玩意……谁不知道你那点把戏呀?什么都干得出……当谁傻呀?把猫塞进花盆里放干了血,喝饱了就拎着那鬼样东西丢进洗衣机里去,啊呀呀,脖子扭断了呀,眼睛掉了呀,脊柱也折了,还把你吓了一大跳呢是不是?回来抿抿嘴巴,谎话编了三大桶!那乖得……乖得好像嘴边揩去的是蛋糕上的樱桃酱,是不是?还还还……还还还墙皮和土……”
“那是真的!”她叫着。“那是真的!我咽得好辛苦!是真的!是真的!是让我骄傲一周的!”
“是,你骄傲一周。你骄傲一生都可以。我错了,我从一开始就错,我就不该管你,这是个什么地方?啊?这就是个‘错地方’。你就是吸血鬼。你再好、再无辜、再不像,你也是。去找他去找他吧,你不但应该去找他,你还应该以找到他为一生最重要的志向。去吧,别再哭了,你的眼泪流不完吗?”
“别这样说求你了!”她叫,“我忍不住了,去他的!我现在不会了!现在不会!我不伤害猫,要伤害人吗?”
“你觉得你伤得还不够吗?我都听见有人说过!你就是没有办法!跟你在一起的人就没有人能够快乐!没有人能够快乐!没有人能够快乐!大家只能绕着你转,神经全都绷得紧紧的!你就在一边磨牙张嘴,看着谁走过来,便咬谁一口。”
她像个被突然剪断了线的木偶一样在床上翩然跪倒,被她一直以来最为惊惧的话一击命中。如同木钉穿心,身后的十字架已经与皮肉粘合一处,犹如血肉横飞也卸不下的沉淀负重。撞击声破空而入,门被打开,老账房走进来。
落儿面色如纸。牙关紧闭。她左手纤细手腕处的鲜血如沙漠中几近干涸的荒泉。她一动不动。身上开满了鲜红的花朵。她独自坐着。她的长发披拂如幡展。她的长发披拂如泪落。
“你以为你是真的?……”她微弱地说,“我又有不知道什么呢?是我把自己骗过了……把自己骗过了……你是我想的……在和我说话而已。不然还能怎样的呢?谁会来?没有人会来的。我又怎么能去招引别人呢?吸血鬼太容易伤人啊……”
第三天晚上,落儿醒来了。被子很厚。眉心清凉。身体轻软,仿佛会像风筝般随风打晃。被沉重的被子压着,她觉得很安全。
一滴水滴在她的眉心,带着微微的、腐朽的气味,在上方黑暗中滴水嘴怪兽充满讥讽的注视之下她用力昂起头向上望去。吧嗒。她眨眨眼。吧嗒。屋顶终于还是漏水了。
就在这个时候,她终于听见了窗外的声响。第五盆水仙花。第五盆水仙花正在枯萎。一道、两道、三道。用他修长锋利的手指,如赐予每一段脖颈的,优雅小巧的伤痕。
第一道伤口轻轻蔓延。滴滴嗒。滴滴嗒。带我走的人,有绝世的容颜。
第二道伤口轻轻蔓延。滴滴嗒。滴滴嗒。尖牙齿挥舞,如大蝴蝶蹁跹。
第三道伤口轻轻蔓延。滴滴嗒。滴滴嗒。醒不来的梦,梦里只有欢颜。
须臾,声音消失了。如电影中等待宣读结局的安静空场。水依旧不断滴下,像她女孩儿气的宜人寂寞化为了触觉。然后她闭上眼睛沉睡,窗外没有再传来声响。
第二天早上,落儿早早起床。吃了早餐之后,她来到周末集市上,集市上在卖彩色的小熊软糖。
“这个。”她指着糖果定定地说,“所有的。这一整罐子。”然后抱回了屋内,放在原先水仙花在的地方。她不再养水仙花了。
走廊已经被蛛网和崩塌脱落的墙灰占据,我向着走廊深处走,每一步都好像在这些毫无生气的存在中艰难突围。她的房间里透出仅有的光线仿佛在布袋中飞舞的萤火虫。
推开门的时候,我默念:
一开始就是个错误,从多久开始呢?从她认识埃狄亚,或者从她决定做她自己的叛徒的时候,都可以。这两个,哪一个胜利了,另一个就是错误。这样说来,从她认识到自己身体中的力气时,一切都不可避免,她的眼前有无数条路,但无数条都是歧途。
他们在人群中听凭天性认出彼此,在紧张的追逐与躲藏中终于相见。他们相互亲吻,他们相互饮血,他们相互见证,他们相互拆毁赖以独自生存的城墙,他们再不相见,他们相见于歧途,他们相忘于歧途。他们谁也不告诉,他们什么也不说。
天已经亮了,紧闭栓锁的窗扇和杏黄色的百叶窗帘通透单薄,上午的天光告密般爆裂而入。观察室狭小而独立,窗口的窄轮廓在一侧平整的墙面上映成灰色的碑。在那片阴影之下出现的薄薄人形,透满了模糊的黄色微光。我试图描述这种在日悬之时一再上演的颜色,规律循环,了无终结,填充着空间,如一张难过的脸。
她换上了白色的棉制服,和这里的其他人一样,显得苍白安静如白瓷瓶中断绝光线的植物。那双眼睛依旧如同被掏空的洞穴,她的视力是什么时候坏掉的?来这之前?一只眼睛只能看见模糊的轮廓,是哪只眼瞳来着?从外面看不出来。从外面看不出来的东西太多了。
我叫她。落儿。她坐在床边拉耸着双腿,看见我,她从床上站起来。我用肩膀掩上门,把怀中透明的糖罐子放在窗台上。五颜六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