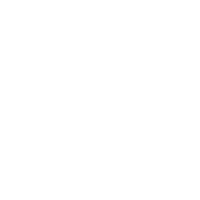吃煎饼(运河故事之九十四)
暑期和家人自驾游去蒙山,在附近转了几天,回来后议论最多回味良久的竟然是煎饼。
的确,那几天几乎顿顿都有煎饼,宾馆早晨的自助餐上有切割成块码放整齐的,路边农家乐的餐桌上有一摞摞叠放在筐里的,有卷了大葱一根根摆在盘里的,即使是蒙山脚下和半山腰上,也随处可见现场制作煎饼的路边摊,卷好的、现卷的,都有,瓷罐里有浓稠味醇的酱,柳条筐里堆着洗净的葱,旁边支着热腾腾的铁鏊子,散发着浓浓的乡土和烟火味儿。几天里我们全家都过足了煎饼瘾,儿子也由最初对大葱的抗拒变得离开煎饼大葱就吃不下饭的地步。
相对来说我对煎饼还是比较熟悉的,几年前曾经在临沂老区一个偏远的村子里参加扶贫工作一年,那年工作在村里,吃住却在十几里外的镇里,镇食堂的邵师傅四十出头,每天都会为我们准备一些煎饼,竹筐里盛着,上面盖着白色笼布。煎饼是他自己烙的,有时也从镇中心集市上买来,配上自己做的小菜,必不可少的是卷在煎饼里的大葱、花生碎、芝麻盐、油煎的豆腐,有时还会有油炸后又压扁的知了猴儿,把煎饼卷成圆筒状,每次吃饭都是一顿兴趣盎然的撕咬,龇牙咧嘴又乐此不疲。也难怪,临沂的煎饼不同于别处,软、糯、香,适合卷着吃、撕着吃。想起那一年入乡随俗的经历,几个人人手一个卷了大葱的煎饼,一只手握着,另只手托着,围坐在圆桌周围,撕扯咬嚼,大朵快颐,至今记忆尤深,常为戏谑谈资。
再往前追溯,与煎饼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应是小时候从沿街换缸那些人手里换来的。
家乡紧挨着京杭运河,因灌溉方便,家家户户种植水稻,成为远近有名的“运河稻”产区。每年秋收以后把稻草垛在场院,不几天就会有人拉来大缸换稻草。都是些壮实的农家汉子,据说多是从嘉祥、泗水等一些陌生的地方,步行几十甚至上百公里来到这里,用加长的地排车和手指般粗的苘绳捆扎了大大小小的砂缸。我们需要砂缸存粮蓄水腌咸菜,他们要用稻草打苫子织箔片,各取所需,所以他们会在秋收后的某一天三三两两地来到村里,黝黑的面孔,长途跋涉的疲惫和困倦,把地排车停在村口或路边,说着我们听不清楚的外乡话。我们小孩子故意从他们身边走过,惊诧于他们是怎么从遥远的西边一步步挨到我们村里来的。
到饭点儿了,他们就停在哪家门口,端着茶缸进门要一缸白开水,从布袋里抽出一摞煎饼大嚼一通。虽然只有白开水和煎饼,但他们吃得津津有味,还把掉在衣服上的煎饼渣捡起来放在嘴里,有的一手拿着煎饼撕咬,另一只手放在煎饼和嘴巴的下边,专门接着落下的煎饼渣,然后一把捂在嘴里。有时把煎饼撕开放在开水里泡着吃,看着好像很硬的煎饼一遇到水就绵软了下来,就像家里的那只小猫,看起来凶巴巴的,只要是把手轻柔地放在它背上,它就立马俯低腰身,像抽去了骨头一样。我们对这种像撕纸一样的吃法很好奇,并从他们用力撕咬煎饼的夸张和享受中产生了越来越浓的饿意和馋意,开始垂涎于这种能叠在一起吃的像黄纸一样的东西,还有那些簌簌落下的渣渣,就站在旁边盯着看。有时他们会撕下一块递给我们,笑眯眯的,让我们消除本能的怯生生的小心,接过来放进嘴里,贴在舌头上的感觉竟是酸酸的,腮帮子瞬间膨胀。
也许是家里大人看到了我们的好奇和眼馋,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就开始拿家里的馒头、玉米饼、地瓜窝头与他们交换煎饼,他们似乎也很乐意这么做,于是每逢秋末季节,我们也能吃到几张煎饼,像大人偶尔买来的糕点一样,一次只能吃一点,舍不得一次全部吃完。好东西是要慢慢品尝的,可不能学猪八戒吃人参果。大人经常这么说。
依稀记得当时吃的煎饼不是我们在临沂吃到的那样,很硬,发干,有种酸味。我一直以为煎饼还是新烙出来的好吃,软软的,甜甜的,有点儿糯,有劲道。现在超市的特产专区摆满了各种包装的煎饼,质地、颜色、口味更加丰富多彩,但似乎远不如儿时吃的煎饼,那样诱人,那么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