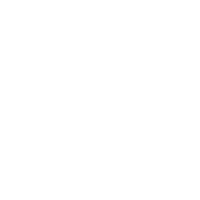奶 奶
奶奶去世好多年了,她的形象随时间渐渐远去,远得都有些记不清了,现在能想起来的也只是一个大概,如奶奶一年四季都穿的是黑色的大襟衣服,只是季节的不同而大襟衣服的厚度不同而已。在我的记忆中,奶奶夏天是黑色的大襟单衣,春秋是黑色的大襟夹衣,冬天是黑色的大襟棉衣。除大襟衣服外,还记得奶奶有一双很小很小的脚,脚上绑着很长很长的布,晚上洗漱时要好长的时间才将布解开。小时奶奶洗脚时我们几个总是围在木盆边,看奶奶与我们不一样的脚,奶奶总是说:你们脚大,脚大踩得江山稳。这是我记忆中奶奶最有文采的一句话。
如果静下心来细想,奶奶也能慢慢清晰些,如奶奶的牙齿都掉光了,所以嘴瘪;奶奶的头发几乎全都白了,只是在白发中有几缕既不黑也不白的参杂其中。奶奶的脸很黄,没有肉,能看到的只有皮和一块块老年斑,还有额头上皱纹,一条一条的,像干裂的小水沟。奶奶虽然老了,但眼睛很好,还能做针线活,穿针引线都不是问题。奶奶每年最忙的时候,正是冬季的农闲时期,那时农村都兴织布,奶奶织布的手艺特别高,每年这时节奶奶便成为全村的主角,那些嫂子、婶娘、大妈们都要围着奶奶转,这时奶奶特别威风,指挥着全村的妇女,将一根根的线变成一匹匹的布,所以那时我觉得奶奶很了不起。
奶奶姓夏,十里八乡的人都叫她夏大妈。我不知道奶奶的名字,我一直也没有听到有人叫奶奶的名字,我只知道在奶奶的工分本上写着夏氏老人,直到她死时,她的灵位上写的都是夏老太君,这就是我知道的奶奶的名字,所以我到现在都只知道奶奶叫奶奶。
从我记事时起奶奶一直都下地干活,用自己挣工分来养活自己。也是从我记事时起奶奶就是一个人生活,按理说奶奶应该我们生活一起,因为她只有我父亲一个儿子,她和我们一个生活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她没有,要一个人过,一直到她不能下地干活时都是一个人。村里好多人都劝她,我也曾听到父母要她和我们一起过,但她不同意。后来我知道了,她说他们(指我父母)孩子多负担重,她不愿意给我父母增加负担。她说能挣点工分就挣点,到动不了的时候再让他们来管。奶奶真的是这样,直到她真的不能动了的时候她才停止挣工分。从奶奶不下地了之后,奶奶就没有真的不行了,不是病了而是老了,老得只能坐在家里,走路都很不方便;后来就只能坐在床上,再后来下床都困难,最后就死在她那张床上。
我最后一次见到奶奶,还是在她要去世的前两年。那时奶奶已有几年不能下床了,我回家过春节,带了些对奶奶来说算是新奇的点心和水果。我到奶奶的房间,看奶奶再也没有了以前精神气,脖子好象已支不起自己的头,倦缩在床上。我走近奶奶,俯身去看她那低得看不见脸的头,我看到的是零乱白发和黑布衣服。我有些不相信这就是我奶奶,曾经声音如钟,做事如风似火的奶奶。
奶奶虽然抬不起头,但耳朵还是特别灵,我只叫一声奶奶她就听出来是我。她让我坐在床边,她说我眼睛已经瞎了,什么看不见了,要我过去让我摸摸。我将头伸过去,她用粗糙的手摸摸头,摸摸脸,再摸摸手,一边摸一边说,长得好长得好。说句不该说的话,奶奶的手真有些象鸡瓜子,一点点肉都没有,除了起了绉的皮就是骨头,尖尖的,粗粗的,摸在脸上象砂纸一样磨脸。奶奶非常高兴,我拿出给奶奶准备的礼物,她又高兴又责惫。说现在挣钱少,城里花钱的地方多,以后回来不要买东西了,多回来就好。遗憾我没记住奶奶的话,没想到那是奶奶最后一次与我说话。
奶奶多大年纪我不知道,只是听说她大概是民国初年的人,到九十年代初才去世。像奶奶这样一个旧时代的农村老妇女自然不会有多少故事留下来,我知道的是奶奶二十六、七岁就守寡,听说一身生了六个孩子,最后留下来的只有我父亲和一个姑姑。
自从我记事起,奶奶讲得最多的只有两件事,一是她一生体面的安葬了三个男人,再是她跑反(就是躲避日本兵,我们那里称为“跑反”)的事。关于三个男人,一个是她的老公公,我的太爷;一个是她的丈夫,我的爷爷;再一个就是她的大大儿子,我的大伯。我的太爷和爷爷是怎么死的我也不知道,大伯的死我是知道的。大伯是抓壮丁出去之后就没回来,死后尸体都不知道在哪,更不知道死于什么地方,但奶奶还是为自己的大儿子举行隆重的安葬仪式。每当奶奶讲起这件事总是哭个不止,而且是大声地痛哭,尽管已不知道过去了多少年,但眼泪象泉水一样,涌。每当奶奶这样痛哭时,我虽然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但知道奶奶很难受,就静静她的眼泪。
奶奶说这三个男人主要是说她如何体面地安葬他们,她办事的场面一点也不比别人家差,大碗的肉,大碗的酒,让客人满意,自己也体面。我记得很清楚,奶奶说这事时只要母亲听到,她都要在后面嘀咕,“一辈子就说死人的事”。我认为奶奶有理由拿出来说的,因为一个在男权社会里的孤独女人,一个靠种植水稻为生计的农耕女人,还是一个带着一群孩子的寡母,她以不输给任何完整家庭的形象,出现在邻里面前当然值得称道。
再一件事就是她带着几个孩子跑反的事。奶奶一共生了六个孩子,后因不断夭折而只剩下父亲和姑姑。日本侵华时我的家乡是敌占区,日本人常到乡里烧杀抢掠,每次日本人来时全村人都要跑出村外去躲藏。别人家人多,能将值钱的财物和孩子都搬到村后的山里去,但奶奶不行,她虽然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但孩子多且小,她怎么也不起来。没有办法,她只好将小的装进箩筐里,肩上挑着;手里牵着大的,跟在别人后面拼命地跑,但还是不行。她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办,就跑到我爷爷的坟前(她说我爷爷坟前长满了又密又高的刺——荆棘,人可以钻进去)去哭,边哭边将孩子赶进荆棘。她说她实在没有办法了,也不知道日本人(她说的是东洋人)会不会看到她们,她只好和孩子躲在刺丛里。她说哭还不能哭出声来,怕日本人听到了;孩子们也吓得哭,她就用手捂着孩子的嘴,但嘴多捂不过来,她就让大的帮着捂。就这样一次次跑反,一次次逃难,好在从来日本人被发现,她说:是你爷爷在天有灵,在地下保佑我们。
奶奶非常勤劳,当然也不得不勤劳,因为她不勤劳就会饿死,而且还是一家人都会饿死。我们那里都是水田,种的都是水稻。水田里的活都是男人干的,但奶奶没有男人,那些活全得要她来做,风里雨里水里泥里全是她一个人,我真不明白,也想不出她那样小的脚是怎么在水田里干活的。
可能正是因为奶奶什么样的活都能干,所以才炼出她结实的身板。在我的印象中奶奶的声音非常大,可用宏亮来形容,她的脚虽小,但走起路的快而有力。她一生很少生病,也从不不吃药不打针,就这样活了八、九十岁。记得有一次奶奶生了一场大病,大哥要接她到县城去看病,她就是不去,说怕死到外面了;也不打针吃药,怎么劝她不顶用,她说她一生都打针吃药的,要让她打针吃药还不如让她死。家里实在是没有办法,只好问她想吃什么。她说只想喝汔水,大哥就不断的供汽水,没想到喝了几月的汽水,竟将身体喝好了,病奇迹般的没了。这是真实的,令人不可思议的奇迹。小时曾听母亲说,奶奶年轻时很强势。我想应该是这样的,要不她一个女人怎能在男权社会中生存下来,尤其是我爷爷又没有兄弟姐妹,在那种无依无靠、举目无亲的环境中若再不强势,想活下来都难。
奶奶一生没有向我们这些孙子们要过什么东西,更提出过什么要求,在我的记意中她只提过一件事,就是要看火车。奶奶一生也没出过家门,更说不上到外地,她只是听人家说火车很长很大,能坐很多人,所以想看看火车是什么样子。大哥当兵回来以后在县城工作,就要接奶奶去看火车,但奶奶没有去,说等他将工作安静了再去;等大哥结婚时又接她去,也没去,说等大哥有孩子再去;之后奶奶老了,走不动了,大哥说用车子接她去,还是没去;后来,我们几个孙子将一切安排得好好的,但她就是不去,说什么也不去,她说怕死在外面,不能回家了,就这样直到她老人家离开我们也不知道火车是什么样子。
奶奶去世好多年了,我们只要提到她老人家,我就想到奶奶一生没有看过火车。
201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