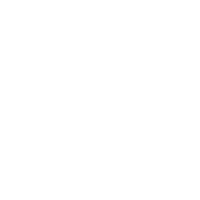王家有女
王家有女
没有院落的家
村子在东边,家在西边,家与村子隔了一道深沟,据说这是多年前的大道。没有院墙,只是孤零零的三间挂砖面儿的蓝砖房。家的四周也再没有邻居住户,房前是清水塘、房后是杏花林,西边是盐碱地长着一丛丛红荆和一些不怕盐碱的小草。这就是解放那年,父亲在故乡买的房子,他是想着有一天老了、漂泊不动了,好落叶归根。那个时候还没有我,到了一九六二年,我出生之后被母亲抱回这里,从此这三间房就成了我的暖巢、我的家....木头的门很结实,门栓也很结实,这就是娘俩生活的最得力的安全保障。大清早一开门,周围几里地之外的村子豁然在目、一览无余。
母亲的坚强
母亲那个时候四十五岁,说大也不是大岁数,说小也不是小岁数,我身长尺半毛重五斤。人不大,我哭起来到时响亮得很,而且常常不分白天黑夜,说哭就哭。母亲没有足够的奶水喂我,所以饿了我就抗议,哭起来没完。要是白天还好过一点儿,母亲总会想办法烧点儿米汤之类的东西喂我。要是夜里哭起来母亲就惨了,找不到合适的食物,乳房又瘪瘪的,加上四周黑咕隆咚,实在怕人、豆油灯的小火苗昏昏然将什么家什的影子映到墙上,夜风吹来飘忽忽鬼魅般的更叫人毛骨悚然。每到这个时候母亲就大骂起来,骂完了我就骂父亲,怪他不该把娘俩弄到老家来,她说这和王三姐住寒窑无异。她骂起来,我就不哭了,瞪着惊恐的眼睛看她,夜里毕竟是夜里,功夫一长。我也就睡着了,母亲见我不哭,也就赶紧搂着我入睡,有粮没粮等天明了再说.....
天一亮,母亲首先要到村外几里路的地方去挑水,我怎么办呢?母亲肩上挑着水桶怀里抱着我,去的时候是空水桶这样还可以,回来就不行了。母亲把我撂在地上,担着水桶走一段路,然后撂下水桶回来抱我,把我撂下再往前担一段水桶,这么几经倒腾一桶水才会担回家,她天天如此。等到我稍大一点,这么做就不行了,我会爬,不是放哪儿就在哪儿原地不动了,母亲不放心了,于是每次担水她就把我锁在屋里。锁在屋里她也不是完全放心,屋里家什多她怕我被什么东西碰着,于是她干脆就早起,趁我没醒去挑水。有一次,我醒来不见了母亲,一只手拽着我的小褥子、一只手拉着洗脸盆爬到了门边出不来,便用手抓那土墙,哭了个一塌糊涂,母亲回来见我满脸的泪和泥心里又不平起来,接着骂父亲。很快,我就会走路了,也能听懂她简单的话,母亲给我做了一身红衣红裤,再去挑水的时候,她叫我坐在门槛上等她,她去的时候渐行渐远,时时回头看着我,我由一个小人儿慢慢变成一个小红标记,我始终在她的视线里,她就放心了。可是渐渐的会走路的我并不是那么老实的坐在门槛上等她,我坐烦了也会溜达溜达,没有其他孩子来玩儿,我也不会走远,只是看到地上有什么就拿起来玩什么。
有一种小草叫香香草,碎碎的小粉花结籽很快,还有一种叫臭地萣,白花略大一些,很美但是味道的确不好闻。这两种不怕盐碱的植物就长在房子周围,前者爱招蚂蚁、后者爱招苍蝇蚊子,而我偏偏爱去招惹它们。掐下花来玩儿,或者连根拔下来拿在手里,这样一来苍蝇蚊子四散奔逃,蚂蚁也就爬到手上,我又害怕起来,连哭带甩。母亲闻声撂下手里的活儿赶过来帮我把手上的小生灵弄干净,搂着我叹息命运的不公平。现在想来,一个母亲带着幼儿,生活在这荒凉贫瘠的村外、住在四面透风的屋子里,样样事情都要亲力亲为,何况还时常缺粮少柴,这样的日子何时是个尽头呢?
父亲在外面谋生,不常回来,家里的米常常接济不到,母亲就外出捡些山芋萝卜来补充。她用胡萝卜做馅,山芋面做皮儿包饺子吃,别说这道佳肴如何难做,山芋面儿没劲儿,是不好合成团的,再擀成饺子皮儿,那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可是母亲能做到,她说山芋面粘性差就加一点儿榆树皮晒干轧成的面,和好再省一个时辰就可以擀成薄皮儿。且不说这有多么费事,如此材料做成的饺子味道如何可想而知,好在那是只图填饱肚子,不讲究味道。烧饭用的柴也要去捡,有时候捡回来乱蓬蓬的茅草、有时候捡回来潮湿的树枝、有时候捡回来细碎的树叶。前者火苗一轰老高,分分钟就燎完,常常是锅里的水还没动静火已经熄灭。潮湿的树枝就相反,直冒烟不冒火,常常熏的人涕泪交流。至于细碎的树叶则介于两者之间,总是把火埋住,要不断的拉风匣才行,结果是浓烟灰尘满屋飞。现在想想只是为了做饭,母亲也该够烦躁的!母亲这捡柴的日子持续了许多年,到我记事的时候,印象最深的是,夜幕降临,母亲还迟迟不回,以至于我自己在家害怕得不行,心里默默地想:到睡觉的时候母亲一定能回来,因为她是一定要搂着我睡的,“睡觉的时候”----那就是我心中与母亲不见不散的假想地。母亲回来匆匆做好饭先把我喂饱,剩下是多是少是凉是热母亲草草充饥。小孩子天性无忧,吃饱了冻不着就开心、淘气,或者把屋里弄乱或者把自己弄脏,母亲着起急来看我一脸萌萌也就破涕为笑,把我收拾干净让我看着她做事情。
其实,母亲不是个终日被陷在柴米油盐里的人,她有她的爱好、有她的追求,尽管她不懂得那是追求,她只知道是喜欢。她有一门儿绝艺一直持续到老,那就是剪纸花。她剪得狮子月亮、花鸟虫鱼形象逼真、栩栩如生,深的街坊邻居喜爱,谁家娶媳妇办喜事都少不了请她剪花,常常获得满门宾客的啧啧赞赏,喜庆的婚礼上那堪称一道别样风景。母亲为乡亲们剪纸花,那是给人帮忙成人之好,完全是为婚庆锦上添花,不会收取人家半点礼物。母亲第二个爱好就是背书唱京戏,母亲识字不多,背书也是源于她小的时候舅舅们口口相传,母亲记忆力特好,她交给我的许多儿歌我至今记忆尤新。母亲会唱几段京戏,字正腔圆,尽管有时候调儿不准确,但是母亲非常的认真、投入,看得出她是领会了唱词的意境并被深深的打动了,她是从心里唱出来的。母亲第三个---换个说法,说是习惯吧,她每天早上一定会去屋后杏花林里梳头。母亲天生丽质,皮肤白皙容貌端庄,有着一头乌黑的长发。杏花盛开的时候,母亲解开乌发拿把梳子,行走花间长发飘逸,形态婀娜,她边走边梳,那真是花中人俏丽,人伴花更娇。
在这里单独交代一下母亲的第二好:儿歌和京腔。到我三四岁的时候,我就能听懂母亲的话,母亲哄我的方式由观看墙上无声的花影变成了有声故事。母亲没有上过学,她有三个哥哥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念书是男孩子优先,因为他们将来要自立要养家糊口,上学是必须的。额女孩子就不一样了,女孩子将来是别人家的人,自有丈夫来养,所以读书就不那么重要。这穷人家最实际的居家打算剥夺了母亲读书的权力。母亲只认得父亲和哥哥的名字,可是她背起书讲起故事来可是滔滔不绝,而且你永远都听不烦。
“背背书包上学校,见老师行个礼,见同学了问声好,相亲相爱真热闹。小孩子,回家早,看见爸爸就说爸爸好,看见妈妈就说妈妈好,爸爸妈妈点点头:好孩子,你也好!”这是迄今为止我记忆中完整的一段,这一段母亲后来照例背给我的孩子听。“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小轱辘呀,小棒槌呀,守着一大堆,爹爹妈妈的小贝”,“头戴红缨帽,脚穿咯噔鞋,咯噔咯噔上楼台,楼台上一汪水,湿了小姐的华裤腿儿...”“王大娘在家上鞋脚,忽听得门外狗声咬,伸手打开门两扇,一看是丈夫来到身边....”这样的儿歌故事数也数不清,这是陪我长大的最得力的精神食粮。
母亲的京戏印象最深的要数王宝钏的故事,因为她常常叨叨自己的境遇就好比王三姐,唱完她会讲给我听,说王宝钏本是皇帝的三公主,只因投绣球招亲,扔出去的绣球打到了穷人薛平贵,父亲断绝了她的一切供给,三姐住进了寒窑里,挖野菜为生。丈夫薛平贵去打仗一走十八年,熬到丈夫回来却领来了新妻子。那位二太太倒是非常的贤惠,她对苦命的王宝钏说“您为大我为小,您为正我为偏....”。他们将王宝钏接出寒窑,送上了皇后的宝座,不料王三姐只享了十八天的福就故去了。长大后我才知道这是母亲版本的武家坡,至于里面的故事和正统版本有多少出入,我没去考证过,也不想接受其他的说法,我钦佩王三姐的坚守、韧劲、和顽强忠贞,我以为母亲讲的是最好的。
母亲第二个打动我的故事就是曹庄和他的母亲,曹庄去打柴,母亲送至门口叮嘱“儿啊,有柴无柴你早早的回来....”每每想到这句话, 我的脑子里就会出现一个佝偻着身子的白发母亲,手扶门框对即将出门讨生活的儿子那种无限牵挂、那种恋恋不舍....。这个故事也一直影响到我:年迈人是多么的不舍儿女!以至于我终生没有离开母亲,直到她寿终正寝。
还有三娘教子的故事,说是大娘生了儿子、二娘养了儿子,她们在老员外故去之后都耐不住家贫,相继离开。只剩下三娘舍不下孩子留了下来,忠于这个家的还有一位老家人,一家三口惨淡生活。小孩子顽皮不肯好好读书,三娘苦口相劝“儿啊,还是读书高.....”“杜树没有杨树高!”孩子就这么回应母亲,而且一蹦老高.....。三娘是多么的用心良苦!
母亲的操劳、母亲的精神、母亲的坚强、母亲的故事....伴我到老,磨砺了我永不向困难低头性格。
记忆里的花棉裤
不管大人的日子有多波折、有多清苦,小孩子的成长不会延缓半步,只是这成长的过程中感染了一些孩提时代不应有的痛楚和忧虑、少了一些顽童本能的欢愉和顽皮。那个时候冬天特别的冷,我们的家前后左右都没有邻居,四面没有一堵可以挡风的墙壁。一到冬天肆虐的北风就直接搡进屋里来,木门不够严实、窗户是纸糊的,窗户纸时常被大风撕成纸屑飘散远去,剩下的黏在窗棂上呼啸、拍打,每个冬天母亲都要糊好几次窗户屋顶的椽子缝里也一样向屋里灌冷风,晚上睡觉,母亲把我搂进棉被里,母女俩把头蒙严实,她说还能捂出汗来,而炕脚下的便盆里冻成厚厚的冰。
冬天,母亲最要紧的事儿就是保证我不受冻,给我做棉衣就成了她的头号使命,棉衣棉裤能做多厚就做多厚。做棉衣的工序是把衣服的里和面周遭缝起来,找个适当的地段留一个口儿,一遍棉花续好之后从那里翻过来,这样衣服的正面就寡净漂亮不露针脚儿,母亲给我做的衣服常常是翻不过来,时常见她将袖口或者库管口塞到里面然后用擀面杖使劲往外顶,等到衣服翻过来,她就像取得了什么重大胜利似的,一脸成就。这样做成的棉衣我穿在身上胳膊腿儿就直挺挺的了,那棉裤就是我不穿,它自己也站得住,好在我也不是爱闹的孩子,不活动也没关系,不冷就行了。那一条紫色碎花的棉裤记忆尤深,房前是一簇簇臭地萣的花,还有红荆丛那似云非云的细小花朵,我穿着花棉裤在花丛中转悠,花和人儿就相得益彰,十分的默契,母亲坐在凳子上做针线或者剪纸花,不时地抬头看看我,她怕我走远,其实我不会走远,不会离开她的视线。寒冷的冬天,就在这和谐的花从里、在慈祥的母亲的视野里暖暖地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