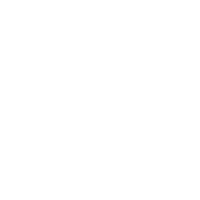院落里消失的那些树
那天坐在东屋的平房顶上,静静地看着我家的院子,左边的台阶上留着13年的那个身影,13年前母亲过世,无知的我坐在房顶的台阶上无喜无悲,墙根下一个行人路过,轻轻一声叹息是说给我听,“她好像她妈妈”。这是那段岁月里记得最清晰的一句话。
那一年妈妈种在堂屋前面的一株杏树,已经郁郁葱葱,往后的许多年,那颗杏树以无比旺盛的生命力肆意生长,每到春天开出满树满树的白色杏花,杏花落后,是满树的果子,那些年家中院落长期无人居住,杏子生长时节是鸟儿的天堂,所以往往杏子还没熟透,就已经被鸟儿吃的所剩无几,等到了秋天之后,地上满是杏核。
有一年爷爷扛了农药桶站在高高的杏树下喷洒农药,那棵树已经太高,农药所能触及的地方十分有限,即便这样,那年我们收获了许多杏子。
那一年,奶奶搬进我家的东屋,长久的在这里居住了下来,她没发伸手去攀折树上的杏子,只能等它自然落下,她去地上一颗一颗捡起来,放进筐里,等我们回来吃,可从来都没有等到过,我们每次回来时,它们早就坏了,所以每次看到的还是杏核。有一次,我在杏子成熟的时节回家了一次,奶奶赶紧拿出收集到的杏子给我吃,我拿了一颗没有被小鸟啄过的放进嘴里,酸酸涩涩并不好吃,又拿有鸟儿啄痕的红红软软的来吃,甜甜软软,很好吃。再往后,花又开了几春,果又结了几夏。
后来爷爷迎来了人生的最后一段岁月,没有人再背着农药桶踮着脚努力想把杏树的每个地方都喷上农药,他脚上那双破旧的黑布鞋再也不会随着他在杏树旁来回磨擦,鞋子上的灰尘终于回到黄色的土地,永远沉寂下去。
再也听不到奶奶数落爷爷的声音了,“都说了鸡刚刚喂过了,你怎么又喂”,“老了还改不了,就那么饿,就不能再等会儿”.......“你干嘛把那颗无花果树给砍了?”
“它在菜园里碍事,遮阳,豆角长不好”爷爷委屈的反驳。
“那么矮,又长在院子最边上,它能多碍事?”奶奶几乎叫起来。
“那么好的一颗果树,每年结那么多无花果,你说可惜不可惜?”奶奶向我抱怨的时候,爷爷只是嘿嘿的笑,他或许也觉得后悔了。
在那颗无花果树左边有一大丛薄荷,那是我小学时候,从上学的路上挖回来的,起初只有一株,以后越长越多,有一次隔壁婶婶来到我家菜园,观摩了一圈,最后停在那从薄荷前,以不轻不重我和妈妈刚好能听到的声音说“这株薄荷都长到我家墙根里了,这会影响地基的。”
那时候我是个极度自卑的孩子,从那以后我开始觉得我的薄荷是有罪的,我不舍得拔掉她,但是开始限制她的生长,然后慢慢忽略她们,我再次想起她们的时候,已经几年过去了,原本生长的地方已经了无痕迹,我在更左边的一株野生香椿树下看到了缠绕的薄荷藤,因在树下和荒草之中,那些盘绕的藤十分纤细,纤细的藤上零星的结着几个更加单薄的叶子,你只有俯身下去,闻到那淡淡的薄荷清香,才能辨出那就是薄荷,那些岁月,我依然沉浸在自己的悲伤之中无暇他顾,那一刻我再次转身,将那片孱弱的身躯再次留在身后,后来她们经历了什么,我不再知道。我不知道她们是否在那漫长的日日夜夜里等我回头,不知道荒草丛中的那些残存的身体是她们等待的最后希望。只是,现在我坐上东屋的平房顶上,向那个角落望去,那里有一株柿子树,而树下再也找不到薄荷的痕迹。
我在努力回想,这棵柿树是何时树下的,我对她有记忆的时候,她好像都已经在了。这棵树,是奶奶的最爱,柿树第一次结果子,只结了一个,奶奶天天盼着它,每次都偏心的去那棵树下小解。那棵柿子终于越长越多大,鸟儿也蠢蠢欲动,奶奶天天提心吊胆,一天,再去看,嗬,你怎么掉地上了。奶奶捡起来,还是硬硬的,拿在手里沉甸甸的,个头也比在树上时看起来大。奶奶小心把她放在纸盒子里,铺上软软的秸秆,等它变软,变红,然后咬在嘴里,甜甜腻腻的。但是奶奶并没有如愿,柿子还没变红变软,它就坏掉了。
此后几年,柿子每年都结,因为树本身很小,结的柿子扳着指头都可以数出来,但这足够奶奶开心,她依然怜惜着她的柿树,等待着绿色枝叶间那几个宝贝慢慢长大,掉落,她弯腰把他们捡起来,奶奶最终有没有吃到过果子,我不知道,我好像从来都没有去问过她,嗯,我一会要去问问她,还要问问她院子西南角落里那棵枣树,还有那棵槐花树去那里了。
其实我能知道那株枣树,和那株槐花树发生了什么。他们曾经并行在那了生长了好多年,一株种在茅房里,为那个露天的茅房撑起一道天然的屏障,一株在她右侧不远处,是一棵有些年岁的高大槐花树,她高高的躯体和枝叉遮住了一半的鸡圈,同时也遮住了那棵枣树的阳光。
不知道是因为长在槐树下,还是什么别的原因,这棵枣树从在我家存在起,从来没结过枣,她每年春天都会认认真真的抽芽,长出嫩绿的叶子,然后再认认真真的开满细细地小花,很快枣花落完,她就开始了漫长的寂静岁月,她看着她头上的那株槐花开满一串又一串的小白色瀑布一样的槐花。然后人们围上来了。
小时候,每到槐花绽放的季节,我们就爬到鸡圈的院墙上攀折着树枝,把一串串白色蝴蝶捋进筐里,高处的花够不到,就用长长的竹竿,竹竿顶上绑了镰刀,把枝头拦腰斩下,我们就在地上捡。摘满满满的一筐,我们家就够了,剩下的随便邻居们去摘。妈妈会把竹筐里的槐花捡掉夹杂在里面的叶子,在桶里洗一遍,再把竹筐放在桶上面放一夜,让水自然控干,第二天早上,我们一起床就能吃到蒸槐花,妈妈用大搪瓷碗,一人盛一碗,一连吃好多天,吃到最后,我就暗暗发誓,明年再也不要喊着吃蒸槐花了,可一到明年,槐花一开就又耐不住性子了,想吃槐花的胃又不安分起来了。
妈妈走后第二年我上了高中,不再经常回家,爸爸也常年在外,只偶尔回来,那个时候弟弟还在小学,还是初中,我竟然不记得了,那些日子他在哪,他在做什么他是怎么过的,我竟然不知道,我没有印象,唯一能想起来的是,高四那年,他突然出现在我的教室外边,他问我要身份证,说他要用我的身份证,他要去打工了,可是年龄不到,他要借我的用,我不记得我当时是否给他。但是现在想想,我的身份证上性别是女,他根本没办法用,还是那时候,那种情况他能想到是只有我这个姐姐,可是我这个姐姐当时又做了什么。
高中之后住校,我就再也没吃到过那株槐树上的槐花,甚至没再见过她开满白色蝴蝶花时的样子了。
而她身下的那棵枣树还在那里,曾经刚种下她时,妈妈常抱怨她,甚至想砍掉。春天来时,院子里各处有杂草冒出来,可是这棵枣树下却从来不生杂草,她好像在用它的方式守护着她的领地。秋天的北方天高气爽,萧瑟的苍凉,知了似乎都厌倦了鸣叫,只有蟋蟀在墙根树下还唱着歌,枣树地下渐渐有黄叶落下,落在平整干净的黄色土地上,枣树的枝干像是满脸皱纹的老人,生命的激情埋藏在遥远的过去,踩在这些落叶上,好像听到了来自远古的空阔和寂寥。
后来我们有了新的厕所,那棵枣树,还有庇护她的槐树,还有她庇护的那片土地消失了,随着她们消失得还有我的童年.
在我更小的时候,我家门前有一棵柳树,是一株歪脖子柳树,她弯曲的枝干刚好为我家大门撑开一片阴凉,说起大门,当时只是在地上竖起两根水泥做的柱子,柱子中间是荆条做的柴门,周围的院墙是玉米秸秆做成的,所以每到秋天收玉米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新院墙,然后院墙一点点变薄,变秃,然后甚至坍塌。
那棵柳树是我童年里最温暖的回忆,我常常一只胳膊攀着她弯曲的那个湾,在她身边转圈。那是我最无忧的一段岁月,竟然那么短暂。但是小学三年级时,家乡发了一次洪水,那年洪水淹没了所有秋天的庄稼。洪水过后,我家那间土做的东屋在一段时间后坍塌,临时改成了菜园,而随着那间土屋死去的还有那棵柳树,来年,我们又发现土屋前面的那棵香椿树其实在那场洪水中也几乎丧命,她撑了一个秋天,慢慢把叶子一片一片的落下,我想她应该是在最后一片叶子落下的时候就死了,因为来年爸爸要将它砍掉时,她的根部已经腐烂了。
如今那棵杏树早已被爸爸砍掉,在她站立过的地方修起了一块水泥地,这块水泥地上现在晒着麦子。
那些消失了的树,是我渐行渐远的童年,也是正在褪色的青春,想及此,内心无比的惆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