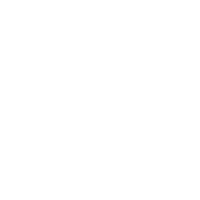记忆中的“年”
如今的“年”大概是从孩子为备战“期末考试”而多起来的家庭作业,在外游子吐槽“12306”购买车票“难于上青天”开始的。
对于孩子来说,“过年”意味着肆无忌惮的玩耍,收到手软的红包;对于游子来说,“过年”是经历过风尘仆仆后,一年到头期待回家的一种心情。
而这种心情,在我的记忆里,是与母亲的油灯联系在一起的。
小时候家里穷,哥哥姐姐我三人都上学,单靠父母在生产队出工是无法养活正长身体的我们姐妹三人的。幸而母亲心灵手巧,自学成才,学的一手好的针线活。
那时候,一般人家平时很少添置衣裤,大人就更不必说了,小孩也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家里的孩子如果是老大才有机会穿新衣,像我是家里的老三,基本都是上面的哥哥姐姐穿剩下的。记得有一年,一个亲戚在年前结婚请客,家里实在没有我能穿出去走亲戚的衣服,只好向邻居的一个差不多大的男孩借了一条裤子来穿。我穿了条新裤子感觉很是新鲜,到了亲戚家不停像别人炫耀“我向哥哥借了条新裤子”,因为年纪小,有点口齿不清,妈妈在一旁不停地给我打掩护“是的,是的,你穿了一条新裤子”!搞得直到现在,年近八十的老母提起此事还记忆犹新,说“幸亏当时的人都知道大家彼此的日子都差不多,大家都心知肚明没人点破而已”。
而只有过年时,一般人家里有点余钱才会给家里人准备新衣。首选是老人,其次是小孩,在我的印象里,大人在过年时的衣服和平常差不多,只不过稍稍干净整洁些而已。那时候,缝纫机是村里的奢侈品,那时候老人穿的衣服类似于现在的旗袍的款式,只不过是宽松版的上衣而已,我们本地人叫“本装”,不知道是否为了和“西装”区分的。一般的缝纫店的师傅要不是手艺不到家,要不就是嫌弃工艺繁琐,所以一般都不接这类活,而母亲就独揽了这一类“本装”衣服的缝制了。
白天要到生产队出工,这类私活只能晚上做了。如今白炽灯大行其道的时代里,现在的孩子只能从图片、影视里看煤油灯了。而母亲,冬夜里,煤油灯下,低头,弯腰,一针一线的动作已深深定格在我的记忆深处。
一家人吃喝洗漱完毕,饭桌旁,昏黄的油灯下,围坐着作业的我们兄妹三人,剩下的一边是母亲的,她洗干净了手,穿好针线,开始在灯下的缝制,大多时候,我们很快做完作业,躲进温暖的被窝,灯影下只剩下母亲一人,她不时用手撩起垂下的额前的遮住眼睛的长发,时而拿针在头上划几下(现在知道是增加铁针的润滑度),记得有一种叫灯芯绒的布料布缝尤其紧密,母亲会带上针箍(俗称“顶针”),在灯下锥的“咬牙切齿”。那时没有所谓的“划粉”(剪裁衣服时所用,类似于“粉笔”),母亲只凭目测来者的胖瘦长短来缝制,所以,灯下缝制时母亲不时停下来,把衣物放在自己或父亲身上比划,或掐紧几寸,或放宽几寸。每每我睡梦中醒来,朦胧中总看到昏黄的灯光下坐着的低头弓腰的母亲,陪我度过一个个漫长的冬夜。
随着年关临近,母亲熬夜也越来越晚,有几次,清晨起床,看到母亲通红的眼睛,一身的倦意,就知道母亲又熬了一个通宵了。可这时的母亲却显得非常高兴,因为全凭手工缝制,一件“本装”棉衣起码要三个步骤,而这才是第一步,接下来还要陈棉絮,盘花扣呢!
说起陈棉絮,这又是母亲的绝活之一,母亲承包了方圆几十里的棉衣的“陈棉絮”的活。所谓“陈棉絮”类似于我们现在往被套里套被子,只不过被套只有一个筒子,而上衣则复杂多了,棉絮要“量体裁衣”,用料要厚薄均匀,绝对是个技术活,我经常在一旁看母亲陈棉絮,自己也跃跃欲试,可是总被母亲推到一旁,那时候,过年添置一件新衣也是一户人家家里的大事,一年忙到头,好不容易省吃俭用给老人小孩添身衣服是件喜庆的事,哪荣得上给小孩练手呢。可每次看到母亲把棉絮陈进衣套里,然后轻轻揉捏厚薄,又轻轻拍打,被夹杂在棉絮中的粉尘弄得咳嗽不已,心里很是难受。母亲也许是洞晓了我的心思,总是笑笑安慰我说“不碍事”。
最后一道盘花扣(我们当地俗称“盘桃”-只是音同而已,不知具体怎么写)的活终于我和姐姐能搭把手,帮上忙了。盘纽扣首先得把布根据厚薄裁成两寸左右的长条,布条长度越长我们越高兴,因为意味着布条要缝接的布缝少。我的工作是把布条卷成三折,然后用针每隔5毫米左右缝缀起来,最终缝成一个长约三四米的长条,记忆中我的寒假是没有作业的(现在的孩子听起来简直是匪夷所思啊),有的只是从早到晚帮母亲缝制“长布条”的情景。缝制的工作是简单而单调的,一天下来,十几个小时坐着,弓腰搭背,腰酸背痛,可我和姐姐谁也不喊一声累,因为我们知道比起母亲,这点累算什么呢,我们白天每缝制完一件衣服的长布条,母亲总会让我和邻居的小伙伴去玩耍一会儿,踢踢毽子,跳跳绳,捉迷藏。而母亲呢,白天一般仍然要出工劳作,只有晚上才是她的个人时间,盘花扣需要手力、齿力和巧力。母亲首先把我们缝好的长条子剪成长度相等的十等分(花扣款式不同,长度也不同),然后用两手像变戏法一样绕来绕去,再辅之以针线勾连,牙齿咬合,一会儿便盘成类似于“蝴蝶”形、“梅花”形等形状的花扣了。记忆中花扣大体有七八种花形,花形不同,费时不同、价钱也不同。像现在一般旗袍上的类似于“一”字形的花扣是最简单的,普通人家都要这种,这种花扣盘起来简单,可缝制到衣服上需要好针线,我曾经也试着缝了一次,稀疏不一,弯弯曲曲,像蚯蚓一般;可母亲缝起来针脚细密齐整,怎么看都好看。如果新衣是嫁衣,一般都会盘复杂的“蝴蝶”扣、“梅花”扣等,母亲需要耗费两三个晚上才能完成一件衣服花扣的“盘”和“缝”的流程。
什么时候我们感觉到年的逼近的呢,也许是从油灯下母亲坐的时间越来越长开始的吧。到大年二十九、三十时,往往家里会坐上三五个等着取新衣服的人,这时候我多么希望我自己化身为一盏油灯,一直照着母亲,陪伴着母亲啊!
如今母亲发已斑斑,齿牙摇动,老眼昏花,提起当年油灯下缝制衣服的情景恍如隔世,走在大街上,各类奇装异服夺人眼目,只是再也不见母亲当年盘着花扣的“本装”衣服了,也许这会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回忆而已了!每天都是“年”,每天都可以穿新衣,只是对于我,我的“年”永远定格在油灯灯影下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