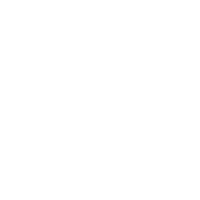蝴蝶和风
1
……簌簌——簌——簌簌簌……风儿轻轻地吹着……
这年夏天比以往到来的稍早,就像刚刚急速奔跑到终点的比赛选手般身上满是炽热。空气中沉闷的气息像极了我苦闷的心情。七月可以说是没有室外生活的存在,倘使在空调房内吹上二十四小时毫不间断的冷气也无法将我心头高考失利的苦楚拂除万分一二。
父母长久以来的期望、朋友发自肺腑的祝福、以及我从小到大的努力似乎都在高考成绩出来的那一刻被窗外的烈阳灼为灰烬,夏风轻轻一吹,那些过往全都灰飞烟灭了。
现在摆在我眼前的有两个选择——复读或是上个三流大学。它们俩就像工工整整镶嵌在一张黑压压的金属方桌上的两个圆形按钮——A或则B?“请选择。”冰冷而又机械性的声音询问我,我分不清是男声还是女声,甚至无法分辨是否属于人类。一个红色一个绿色,无论我按下哪颗按钮都会对我以后的人生差产生巨大的、与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变化。正因我知晓其影响,所以我无法——或是说暂时无法做出选择。
夕暮庄是一个沿海的半度假性质的山庄,离我所居住的城市乘火车需要六个小时的车程,因为有伯父伯母在那里居住,所以我同父母以前也去过几次。说是逃避也好,或是给自己时间考虑问题也罢,我是终究受不了家里沉闷的气氛、亲朋好友们惹人厌的关心与鼓励而选择到夕暮庄度过暑假。
父亲与在夕暮庄的亲戚打了声招呼我便独自踏上了列车。坐在车内仍是酷暑难消,闷热的空气使我暂时忘却了当下的难题,只是两眼发直的望着窗外,似看非看的注视着过往的景象。我不愿去想,也无法去想,此刻我只想到达夕暮庄。
也许是父母提前交代过的关系,到达伯父伯母家后他们并没有向我提及有关高考的半点事情,只是告诉我就当是在自己家,整个夏天只管在这里好好的玩。
吃罢晚饭我便趁着残阳未尽出门散步了。夕暮庄四周环山,对面的丽青山后便是大海,落日的余晖洒在连绵不绝的山峦上熠熠生辉。夕照辉映下的翠绿山腰,恍如在草原中心屹立不倒的高耸的金色巨塔。还有从山那边吹来的海风,它从大洋彼岸穿过广阔无垠的海洋,越过重峦叠嶂的高山来到我面前,伴随着大海的潮湿和山间花草的幽香沁人心脾。那呼呼的风声就像少女在耳旁窃窃私语般萦绕我的耳际。那风儿好似绝美的舞女在我身旁翩翩起舞,在我四周围绕着、旋转着、扭动着……
“喂,别动,请不要动好吗?”
一阵低沉恬静的女声伴随着蝉鸣含糊不清。虽说是个疑问句,却夹杂着一丝命令的口吻。我寻声望去(但不知为何我竟下意识的尽量不移动自己的身体),发现一名身穿米黄色连衣裙,头戴白色遮阳帽,头发微微搭在肩上的女生坐在树旁的木椅上手拿铅笔在本子上像是正画着什么。
“快了,再站一会儿就好了哦。”她再次开口,但眼睛却在我与手里的本子上来回扫动着,不因开口说话而使其目光在我身上多一分停留,眼睛与嘴巴仿佛是两个完全独立的个体。
“好了,完成了。”约过了两分钟后她的目光终于不再来回扫射,而是直盯盯地望着我说。
这时我才我看清了她的脸,那是一副已脱尽稚气但却还不像大人们那么成熟的正处于尴尬年龄的脸。而且那脸白的足以让人心生嫉妒,在余晖的映衬下美的令人目眩。可能是身体保持一种姿势的原因,也可能是我盯着她出了神,我就像看见了美杜莎的眼睛似得浑身动弹不得。
“喂喂,画完了哦,谢谢了。”她说着拿起手中的画本朝我摆了摆。
她的这句话就像咒语般解除了我身上的魔法,身子逐渐变的松弛后我小步向她走去。
“速写吗?”我清了清嗓子向她问道。
“恩啊,你看。”说着她将画本打开,映入我眼帘的是一张站立的侧身少年速写,虽说我并不是多么懂画,但却觉得其动态与画面把握的非常之好,还有那周围轻描淡写勾勒出的景物,可见她画工很深。
“好好啊,画的……真好。”我并不擅长夸奖别人,所以难免语塞。
“刚刚真不好意思,突然叫你别动,吃了一惊吧?”
“还好,只是觉得有点奇怪。”近距离的交谈使我看见她帽子的蕾丝绸带上还有着一个淡粉色的蝴蝶结。
“奇怪……为什么?奇怪吗?”
“当然了,倘若是你好端端地站在路边欣赏着美丽的夕阳,突然不知从哪砸过来一句‘喂,别动’,想必你也会觉得完全摸不着头脑吧。”
“哦,听你怎么一说,倒着实有着那么点道理啊。”她手托着下巴眼神迷离,整个一脸认真思考的表情。
“我说你……,为何突然画起我来了呢?”也许学艺术的人的思考方式与我完全不同,我也不想在一个问题(也许根本算不上问题)上与她讨论,所以随即岔开了话题。
“袄,这个啊。”果不其然,她的眼神瞬间从迷离转为明亮。“我本想画画景物的,但突然看见一名白衣少年笔直的像座白塔般站在夕阳下,余晖照在白衬衫的样子好极了,所以不知不觉的就画了起来。”
“时间不早了,我要回去的,不然他们又有说我了。”说罢她站起身来。
一股淡淡的清香缓缓向我袭来,我不知是花香还是蝶香,或是她的香气。向我说了声“再见”便转身离去,走不几步,她像是落下了什么东西似得小跑回来,而后把画本打开,簌簌的在上面写了点什么后将其撕下。
“这个,就当是做模特的礼物啦。”说罢快步离去,她那白色高跟鞋踩在水泥地上沙沙作响,扬起的灰尘不知会不会将那纯白玷污分毫。
我定眼一看,原来是刚才那张画我的速写画,只是在右下角多了两个端秀清新的字:夏岚。
2
翌日清晨伴随着蝉鸣我起了个大早。夏天的小花被晨露润湿散发出朦胧的光,阳光仿佛从云隙流泻下来似得。在夏日,清晨果然是最舒适的时候,晨光映在身上好似将我全身的疲劳都拂除殆尽。
几只叫不上名的蝴蝶在一大片桔梗花旁辗转飞舞。村庄里的蝴蝶与钢筋水泥架构而成的城市里的蝴蝶是毫不一样的,不仅种类与城市的相比令人眼花缭乱,而且毫不怕人。都市里的蝴蝶总是胆战心惊的在花丛旁起舞,一有风吹草动便展翅遁去,而在这里就算我伸手轻轻触摸其羽翼,它也会懒散地拍打双翅围绕着我的手掌飞好一阵子。
再次遇见她是在那一大片花田里,在这不大的夕暮村里这倒并不让我感到意外。只见她在支起的画架旁,手拿调色盘与画笔站在被微风吹的簌簌作响的草丛中聚精会神的描绘着某一处的景色。
我小心翼翼的走到她的后面,浮现在我眼前的是一张四开大的油画,几朵小花旁有两只蝴蝶形态各异的飞舞着,还有一只正安静地落在花朵上。我感觉她用色非常大胆,就算只是普通的花与蝴蝶也给我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不仅仅是视觉,就连心间的某一处似乎也被其折服。
“画的可真令人心旷神怡啊。”
她扭过头来,先是吃了一惊,随即转过身来笑了笑,那露出的一丁点的洁白牙齿与她白瓷般的肌肤无异。
“昨天被我惊着了,今天倒还礼来了哟。”她字斟句酌的说道。
我沉默不语,无论是她那冷漠的高鼻梁、轻佻的嘴角还是慵懒的眼睛都足以让我着迷。
“你知道我在画什么吗?”她嘴巴微微一动,抛出了一个可笑的问题。
“蝴蝶和花啊。”
“错了哦,不是的。”她嘴角轻轻上扬,但足以让我察觉她的笑意。“我想画的可不是那些。”
“那是?”说罢我沉默不语,等待着她的解答。
“风,是风,是风啊。”
“喜欢风?怎么画?”
“画风啊……”她掸了掸额前的刘海,“空中飞舞的蝴蝶是风,被吹地摇摇晃晃的花草是风,海浪流动也是风……你看,风是不是无处不在、随时便可画出来呢?”
……
随后我和她结伴在夕暮庄信步而行。我们穿过街道,她蹲下身来抚摸流浪的小狗。我们路过小溪边,她脱下鞋子任凭溪水在她那白皙的双脚上流淌。我们登上山坡,她张开双臂紧闭双眼,我问她在干嘛,她只是说:“在和风儿相拥啊。”
灼人肌肤的阳光诱使我们到路旁的香樟树下,在那从树叶间隙流泻下来的微光下歇歇脚。她从路边的小卖部买来了两瓶凉爽的冰红茶递给了我一瓶。
通过与她交谈我得知她是个二十三岁的美术老师,比十八岁的我大了整整五岁。虽说刚刚毕业一年,却有着高超的画工,专门负责美术生的专业课,大学期间是学油画专业的。因为身体不适在父母的要求下来到夕暮庄休养。
她拿起带上MP3的耳机悠闲得听起来音乐。我则身子轻轻后仰靠着椅背,紧闭双眼感受着蝉鸣、木香、鸟儿拍打双翅引起地空气流动、蝴蝶触碰到桔梗花轻微地晃动……
我感觉下起了雪,雪花轻轻落在我的额头上,但奇怪的是我竟感受不到一丁点儿的寒冷。
我想可谓是“暖雪”。
当我微微睁开双眼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她那冷漠的高鼻子。我感到脑袋微微发胀,额前有几滴汗珠。她的手立刻从我额前移开。
“看你睡得那么香,真不忍打扰你。”
我将头艰难地抬起望向天空,白昼已被泼上了一整片橘黄。
“已经日落了吗?我睡的可真够久的。”或许是刚刚睡醒的关系,她那白皙的恍如皎洁明月的脸庞着实令我目眩。
“嗯,今天已经晚了,我要赶紧回去了。”
“明天……或是下次……还会出来吗?”我慢慢吞吞地吐出了一句话。
“好啊,就在庄里的那片花田吧,明天中午后在那里碰头可好?”
“好的。”说罢我看见她高挑的背影在夕阳的照耀下渐行渐远,那影子无限延长直至消失。
3
第二天我仍是起了个大早。但早上丝毫没有外出的欲望,吃罢早餐便在屋里翻翻杂志,听听歌打发时间。昨天她在树荫下听的会是什么歌呢?我脑海里不禁浮现出这个问题。我看着MP4上的歌曲自言自语道:“花海?七里香?风继续吹?……”但这无意义的猜想很快便结束了。
当我吃过午饭来到那片花田时发现她已坐在木椅上戴着耳机画起了风景。那黑白的素描仿佛被她赋予了色彩,既生动又形象。明暗有致、深浅得当、虚实结合。丝毫不比水彩画显得单调,就像是技艺高超的摄影师用单反拍出来的、陈列在展览馆的艺术品。
我走到她旁边轻轻的坐下,并夸她画的桔梗美的仿佛从画中都浸透着清香。
“我画的是风呀,是风。”她字斟句酌的对我说道。
她提议要给我画张素描头像,但想想被她盯着好几十分钟就有一丝不自在便再三推辞了。随后我们又聊了起来。我将今年高考失利、被父母亲人的压力压得喘不过气、在复读与升学间纠结的事统统向她倾诉。
“那么……究竟向不向往大学生活呢?”也许是下午温度上升的原因,她利索的用发卡将身后的头发卡住。
“当然了,我向往着,但又不甘仅仅只上个三流学校,我所向往地是自己的努力得到认可,顺利地考进一流的学校。”
“这不就结了,去复读啊。”
“可是,有了第一次的失败,我就怕了。”话说多了难免口干,我将带来的冰红茶押了一口。“真真切切的、毫不含糊的恐惧仿佛刺穿了我的羽翼,我就像只受过伤的昆虫,再次挥动双翼只会摇摇晃晃、最终凄凉地坠下。我怕,我怕以后都不能——或是不敢展翅翱翔了。”
“也许是因为还未起风呢。”她慵懒的眼神盯着天空,“你现在所要做的便是等待,但又不能仅仅是等待。你要养精蓄锐,稳步向前,加倍努力。只待风儿一起,风向一对,便只需高举双翅,翻转尾翼,拍打着羽翼就乘着风儿飞向远方了。”
振奋人心的无需是香烟美酒。有时候,合适的人的一句合适的话足矣。
我也学着她抬头似看非地望着天空。一只迷途在我们身旁飞舞着的黑色蝴蝶,翩翩翻翻地围绕着我们俩。
“你知道蝴蝶飞舞的方向吗?”她突然开头,而我则露出满脸的疑惑。
“传说,蝴蝶是向着风的方向飞翔的。花草摆动的方向、水面流动的方向、蝴蝶飞舞的方向都是风儿的方向哟。”
我抬手伸向那黑蝶,不料还未触及到便翩翩飞走了。我们在花田里散步,她想俯身摘朵桔梗花,但忽然起风了,花和花叶沙沙作响,随风摇曳,从她的手心里逃遁,一片飞舞地叶子划破了她的手指。
“风儿起,我想到远方去。”她轻声低吟道。那声音有一种雨后被打落的花儿的凄楚。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隔三差五的在花田相见。我们一起游走在夕暮庄的角角落落,从清晨到黄昏。我从亲戚家借来单车载着她在乡间小路上疾驰。我纤细的手指触及在我腰间的感觉是清爽的。她画花、画蝶、画山峦……但她总是说:“风,是风,是风啊。”
一日正午,我们躺在茂盛的夏草上,阳光透过树叶缝隙散落下来,斑斑点点地落在她的身上。樟树摇曳的叶影给她那苍白的脸上衬上了一丝光彩。她戴着耳机,惨白的肌肤与那白的晃眼的耳机线别无他样。如果第一次遇见夏岚时我折服于她白瓷般的肌肤,那么不知为何她的气色越来越苍白,似乎再这样下去风一吹便会随之而去。
也许是看见她那洁白的耳机的缘故,我脑海中突然从记忆的彼端抛出了一个问题:上次我睡着时她听的是什么歌呢?我记得我还为此浮想联翩过。随即我又将疑问由记忆的彼端又抛给了她。
“当时啊,我什么也没听哦。”她思索片刻便解答了问题。“当时觉得和你一起坐在哪挺紧张的,所以只好装作在听歌,其实啊,MP3根本就没有打开。”
我轻轻的笑了起来,不知是笑我自己还是她。
蝴蝶随风翩翩飞舞,她站起身来追着它们在花田里也像蝴蝶一样飘舞着。她追赶着飞翔的蝴蝶,却不知我正注视着好似彩蝶般的她。
忽而风止了。她不知为何也随之倒下,我急忙过去。只见她额前渗满了汗珠,艰难的呼吸着。被汗水浸透的额前刘海在阳光下分外耀眼。
我们坐在木椅上休息了好一会儿她的呼吸方才由急促渐渐转为平缓。我一直望着她却毫无言语。不是我不想说点什么,总觉得她就像一只停落在我肩头的娇弱的蝴蝶,我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仿佛就会让她消逝。桔梗的花叶轻微的摆动着,这时又起风了。
“风儿起,我想到远方去。”她再度轻吟起了这句话。
“那丽青山的后面,就是大海哟。”她抬起冷漠的高鼻子,将懒散的双眼微微睁大说道。
“是啊,离开这儿之前去一次就行了。”
“明天,就明天!父亲快来了,到时候怕是不容易再跑出来了。”她抬高声音,眼睛里多了一抹光亮。
朝霞褪色,天边云彩迤逦。夏风吹起她乌黑亮泽的齐胸长发,额前的刘海在风中晃动的样子美极了。
4
翌日清晨,打开窗户时飞起来的蝴蝶落在窗框上的翅瓣随风飘到了房里。外面弥漫着稀薄的雾气。目力所及,池边的杨柳沉甸甸地垂下润湿的叶子,在雾霭中微微摆动着。
不到中午我便在亲戚家接到了母亲的电话。这段时间父母也隔三差五的打电话过来,但无非也就问我过得怎么样丝毫不会提及有关上学的事情。这次是我主动提出了想要复读的想法,电话那头母亲的声音先是惊讶后转为欣慰。我仿佛看见了那印有浅浅皱纹的脸上的表情变化。
吃罢午饭后我就坐在花田的木椅上等她。但等了许久,除了缕缕桔梗的花香、道道刺眼的阳光、阵阵树梢上的蝉鸣便别无其他。滴滴汗珠从额头不断的溢出,身上就像裂开的木桶般被汗水浸湿。我思忖着,但遍索枯肠却没有半点头绪。
接近落日时分。香樟树下,桔梗花旁出现了她的身影。我问她为何怎么晚才到,她只是急急忙忙地推着我到了汽车站。
我们坐在车窗旁,司机死活不打开空调满车的乘客怨声载道。而她却似乎非常高兴,她打开窗户将脸探出窗外。
“喂,小心点。”我无奈的向她说道。
“我在和风亲近哟!很舒服的,你也试试吧。”
淡黄的草木将山峦严严实实的覆盖,那群山离我们由近变远。
……
因为已是黄昏的关系,海边人迹罕见。这并不是我第一次看见大海了,早在孩提的时候我就随父母去过三亚。但此刻的海却比记忆中的更为清晰,更为真实。
她慵懒的眼神难得变得澄澈。随后她迫不及待地脱掉雪白的鞋子在沙滩上向着海边跑去。潮湿的海风微微将她的裙角掀起。
“风儿起,我想到远方去。”她望着海的那边坚定的说。
“远方到底是哪里?”
“我想到世界各地去画各种各样的风啊。”她的眸子明亮起来,“去日本富士山画吹落樱花的风,去耶路撒冷画古老教堂上流淌的风……”
“去吧,不是你说的吗,带风儿一起,风向一对,就拍打着双翅飞翔远方吧。”
“可是……由于身体的原因,父母一直不让我外出。我哪也去不了……”她那眼神忽然黯淡了下来。
她伸手想抓那风,但风犹如从指缝间漏掉的沙子那样,实实在在地、时时刻刻地溜走了。
带有一丝咸味的潮湿海风不断向我们袭来,我坐在海浪边任凭浪花拍打着我的双脚。海岸那方的落日忽而被一阵乌云覆盖,缕缕细丝从天而降,天空下起了冷雨。
她脸上的表情好似远方阴沉的天空,被雨水所浸透的黑发闪耀着异样的光彩。我们急忙跑到汽车站,但左等右等也不见有车辆经过。雨势渐渐变大,我们便只好躲到海边的亭子里避雨。
“一定……一定要想办法回去……”她的话语伴随着不确切,末梢几乎听不清楚。
我望向阻绝着我们归去之路的丽青,黄绿色的山体在雨水中透着沉沉的死气。雨水冲刷着的道路上许久不见一辆车经过,被大雨洗礼过的湿滑山路使翻越过去成为不可能。黑的一览无余的夜幕降临了。没有星星,也没用月光,甚至连飞舞的蝴蝶也消失了,剩下的只有缕缕的雨丝和不知从何传来的、扰人思绪的蝉鸣。
也许是已经习惯,她脸上的绝望也淡漠了,那越发苍白的面庞使我感到不安。依偎在我肩头的她不断的咳嗽着,并不时轻声呢喃,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我诉说。
迷迷糊糊之间她说好羡慕蝴蝶啊,可以自由自在的追随着风儿飞。可以飞过广阔的山峦和无垠的大海,仿佛风能吹到的地方它都能飞去……
不知是雨水还是泪水,她的脸庞湿润了,那带有淡淡柠檬香味的发香不知为何使我感到不安。她又微弱的呢喃着,说她就像只断翅的蝴蝶,等啊等,等啊等,终于等到我这阵清风,终于可以随着我翩翩起舞了……
“风儿起,我想到远方去。”在这黝黑的雨夜她轻声低吟。朦胧的月光洒在她白的透彻的脸上更加朦胧……
……
清晨,伴随着一阵阵海浪拍打沙滩的声音我慢慢睁开了双眼,但却不见了她的踪影。一股海风袭来,亭子里的一张白纸被吹的飞起。走过去定眼一看,我熟睡时的一副素描头像跃然纸上。
我急忙在海岸边毫无头绪的追寻着。目力所及,无不是阵阵浪花或是重重山峦,寻来觅去,全然不见她的身影!
5
从此以后,我再也没见过她。
我日复一日的在那片花田内等待,却从未寻到她的踪迹。夏天已经接近尾声,白色桔梗花枯萎的部分呈黄褐色,如同被火舌轻轻燎过似得。父母催促着我回去办复读的手续,我总是一推再推。
雨渐渐多了起来。清晨,雨就纷纷扬扬地下个不停。屋檐上雨声淅沥,恍如只有我周围是阴霾的。偶有雷声凛然地响彻四方,复又戛然而止。雨停了,天空漂浮着朦胧的朝霞残片。
雨下了又停,停了又下,来来回回惹人烦。
残暑的闷热使我难以成眠,回忆如癌症般蔓延我的全身,窗外大树上的蝉们还在这季末发出徒劳地嘶鸣。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左思右想,闲极无聊下悄悄出了门。
外面寂然无风,只有充盈于耳的蝉鸣和闲静明朗的月色。那声音凄凉婉转,使得我不得不快步跑起才能使其减轻分毫。黝黑夜色下的花田已不复往日的光彩,我望着前方的丽青山,月光之下如耸立的黑色棺材般透着一股使人不寒而栗的凄楚。
我借着月色向丽青前行,刚上山路,周遭充斥着不绝于耳的蝉鸣与寒意。曲折的山间小路不断损耗着我的体力,不知被擦伤了多少次,也不知究竟走了多长时间,只知道我已艰难的登上山顶。
真真切切的饿意如海浪般不断冲击着我的肠胃,眼皮像被灌足了铅水似得不断下沉,手臂上的伤口内溢出淡淡的疼痛。脑袋里似乎就快断胶了,但我不想就此睡去。
我忽然站起身来,继续向山下前行。下山的路远比我想象中的困难,我必须时刻绷紧神经,不断将满满的困意驱散,倘使向半点疲倦屈服,必然倒头滚下山去。
就在黑夜与白昼相互交融的时候我走到了海边,下山后的我索性脱掉鞋子踩在冰凉的沙滩上。饿意与困感不知何时已经退去,就连手臂上的疼痛也已感受不到分毫,只有眼睛微微发涩。平静的海面上浮现出月亮最后的残影,那皎洁的而又不完全的月影忽而化为她那白皙的脸庞,我睁大双眼细细的端详,干涩的双眼几乎溢出了泪,不知何时连月影也消失了,一切不过是虚妄的念想!
东面的天空已经隐约散着白光,稀薄的太阳渐渐浮上了远方的海平线。在这蝴蝶日益稀少的季节,我看见了沙滩上的野花丛里落着一直黑白相见的蝴蝶。那薄的近乎透明的羽翼带着晨曦的露珠,两条黑色的须向前弯曲着,淡黄的尾翼向后延伸,我的手慢慢向它伸去,忽而拍打其双翼消逝了。
我想找到她。在这最后一次与她想见的海边,我想找到她。但只有阵阵海风不断地拂过我的脸庞,股股海浪不停地拍打我的双脚……
我乘着第一班车回到了夕暮庄,在乡间小路上辗转反侧却仍寻不到她的踪影。我在路上不断地、近乎病态地向人们追问着有关一名白皙的美术女生的事情。不知是哪个人说山庄里是有一个因身患重病被父母安排来休养的女生,但那女生似乎经常偷跑出去,有一次还因彻夜未归而使病情急剧恶化,听说就快被父母带走了。我带着野兽喘息般的声音追问着那女生的住处,眼睛里似乎都冲出了血丝,那人把手指向了山庄的西边尽头,说应该是在西边的那群别墅。
我在别墅群内茫然的徘徊,不知停留了多久,但我确确实实的看见了她。只见她在一名中年男人的陪伴下从一间别墅出来上了门外的黑色轿车,车子缓缓地启动,我不由自主的向着那车子追去。
我呼喊着,但疲惫的身子光是可以奔跑就已是万幸,根本无法发出高亢的呼喊。她把头探出了窗外,不知是我飞速跑动的原因还是为何,她脸上的表情痛苦而憔悴,近乎接近扭曲,全然不复以往的美。
我奔跑着,她哭喊着,车子继续行进着,丝毫没有停下的意思。风在我身上不断呼啸而过,将她那顶白色的帽子吹向走了,忽的飞向我的后方。车子忽然转弯,待我好不容易追赶过去,却发现身处在十字路口,前面、左面,右面。我的身子如牢牢钉在路边的雕塑无法挪动哪怕一步。
忽而风又起了,我望向天空,看见一只花白的蝴蝶朝着前方飞行,我立即迈开步伐,大脑一片空白地、毫无目地追寻着它,但那该死的风却把我眼角吹出了泪水。
……簌簌——簌——簌簌簌……风儿轻轻地吹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