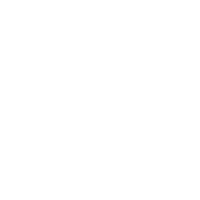村里的叫卖声(河边故事之七十五)
小时候村子里会时不时传来一些叫卖声,高亢嘹亮的,低沉沙哑的;拖着长音的,嘎然而止的;本村的,邻村的,还有从大老远过来带着外乡口音的,都有,有味儿,又耐听。或在清晨暖和慵懒的被窝里,或在傍晚缭绕不散的炊烟里,不经意间就随风飘进耳朵里,有时越来越近,有时又渐行渐远。听的多了,小孩子也喜欢学上一嗓子,甚至像个尾巴一样跟着他们在村子颠簸的土路上,边走边学。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那时候沿街卖东西的还不多,无非是地里产的,自己做的,例如辣椒、豆角、蔬菜种子、豆芽、豆腐之类,“辣椒——”“还有点儿茄子谁要——”,走几步叫上一声,有一搭没一搭的。也有从别处批发来零卖的,蜂窝煤、布料、化肥等。有的提着个竹篮子拎着杆秤步行着来,有的推着辆自行车,也有挑着扁担、推着木车来的。父亲是个木匠,曾做了一些案门,就是鲁西南农村家家摆在堂屋当门用来吃饭的案板,平时半个塞进八仙桌下,吃饭时用,切菜做饭、和面擀面条也都用得着。母亲用地排车拉上几个案门,在附近村庄的街道上叫卖,我就坐在车上,用棉被围着,随着凹凸不平的土路在车上摇晃。那年我也就是两三岁的样子。有一次跟母亲提起这事儿,她一时竟愣在那里,说你怎么还记得这事儿!
还有换缸卖瓮的,多是外地人,往往是几个人一起来,一人一辆地排车,大小的瓮和缸一个套着一个,中间用稻草隔着,用粗苘绳勒紧。来时多是入冬季节,秋收刚结束,家家户户需要用大瓮盛粮食,还要买个小缸腌咸菜,那时这些大瓮和小缸在农村很有市场。。那时钱紧得很,大多是用稻草换,一口大缸要换多少斤稻草,和用钱买差不多。于是一听到“换缸换瓮——”,就会有人应声走出家门和他们讨价还价,几家农妇裹着方巾围着外乡人,七嘴八舌,价格很快就定下来,就有一人跟着去稻草垛,捆扎过称。他们大多来自嘉祥、巨野一带,在我们的西边,口音明显不同,有的把“水”说成“飞”,拖着长音,有时还真听不懂。我们小孩子最感兴趣的是他们吃饭时从布包里取出来的煎饼。因为要长途跋涉,靠脚底板和地排车走上几十甚至上百里路,他们带足的吃物,就是煎饼,黄黄的,像纸一样叠起来,拿在手里直掉碎渣渣,撕扯起来“噼啪”有声,焦脆诱人。每到饭点儿,他们就向旁边的人家要上一碗白开水,拿煎饼泡着吃,间或啃上一口咸菜疙瘩,腮帮子鼓鼓的,发出沉闷的响声。看着我们在旁边馋巴巴地盯着,有时也会撕给一块。后来大人就用馒头锅饼和他们交换一些煎饼给我们解馋,但看上去他们更是乐意。
沿街叫卖的,更多的还是一些手艺人,磨剪子戗菜刀的,锔锅补碗的,剃头刮脸的,修表修伞的,弹棉花的,照相画像的,煽猪买狗的,等等。大多是些细致活儿,做的年数也不短了,推着木车,挑着扁担,挨村挨户地叫喊。
磨剪子戗菜刀的叫声长短有序,“磨——剪子唻——,戗——菜刀——”,电影上经常有这样韵味十足的悠远叫声。通常带着一张长条凳,一头绑上磨石,下边吊着一个小铁桶,准备随时淋水。水是黄色的,溶进了铁锈,双手也像涂了一层黄锈,又黄又涩。他斜坐在板凳的另一头,如果剪子菜刀生锈严重,就必须刮去铁锈。工具是一把一指宽的锋利刀片,绑在一根半米多长的木棍中间,与木棍成直角,他抓住木棍的两头,用刀片在菜刀刃上用力刮几下,不但能刮下锈蚀的部分,还能刮出几条蜷曲的铁丝来,然后依次在粗细不等的磨石上来回地磨,一边磨一边向刀刃上淋水。磨完后冲洗干净,斜着眼睛对着阳光看,大拇指横向划几下,试试刀锋。
锔锅补碗的叫声多是“锔锅锔碗唻——”,拉着长音,浑浊厚重,但后劲儿明显不足。多是上了年纪的,坐在马扎上,有的还戴着副老花镜,镜腿断了,用线栓在耳朵上,围着从脖子到脚的长围裙,补丁一块摞着一块,有的还是皮围裙,怀里抱着裂了纹、破了洞、缺了角、漏了窟窿的锅、碗、盆、缸。使的工具小巧得可爱,小钉锤、小铁钻……。做工也精细,钻眼、上扒锔子、抹灰,轻轻地敲打,好似要把扒锔子彻底地融进陶器、瓷器中去,用力谨慎,落点准确,叮当有声,节奏匀称。完工后加水现场试验,一滴水也不渗,等你说满意了再坐下来继续干活。
沿街叫着剃头理发的也多是一些上了岁数的人,担着一个挑子,一头热一头冷,热的是炉子和水壶,冷的一头是个盆架,上边嵌着或悬着一面圆镜子,支起的挂架上挂着白围裙、毛巾等,下面有个木箱子,几层抽屉,里面整齐地摆放着推子、剪刀等工具。理发的往往短平头,头发黑白相间,胡子也刮得干净,衣服整洁,带着套袖,一看就是个干净利落的人。经常走街串巷,大家彼此都很熟络,听到“剃头刮脸喂——”的叫声,就有人把他叫到家里,或者就在当街的遮风僻静处,放下挑子铺摆家什,抖一抖白布轻轻系在顾客的脖子上。从开始往推子上滴油润滑只到揭开白布理发结束,嘴就没有停过,边剃边聊,什么都不耽误。他知道的也多,除了自己理发的逸闻趣事,还有某某村某某家某某人的某某事,说的有理有据,有鼻子有眼,一切好像都发生在眼前,不知不觉手里的活就干完了,一问一答,一唱一和,谁也不觉得烦,谁也不觉得累。爷爷和村里老人从来不去理发店,就喜欢走街的,一是熟悉,二是价格实惠,更重要的还是活儿利索,服务周到。一个剃头,不仅把头刮得像经了霜的冬瓜一样,还要刮脸、剪鼻毛,最后还捎带上捏肩捶背。小孩子也喜欢,在慈眉善目的老人面前,那一层惊恐也变得淡了,再说还有好听的故事。理完以后取下小圆镜子,绕着脑袋让你看一个遍,决不落下任何一个边角。
弹棉花的是外乡人,经常是夫妻俩,拉着地排车,叫着混沌的“弹棉花喽——”。车里一架箔床,一张弯弓,一支纺锤,除此之外,就是锅碗瓢盆和被褥衣服等,走到哪儿就住在哪儿,往往是借住人家的柴房,要么就是在某个胡同角落搭一间帆布棚子。一天中除了揽活做生意,就是闷头弹棉花,两人各忙各的,每天忙忙碌碌,浑身都是棉絮。我们小孩子很是惊奇,怎么竟能把一些破旧棉絮加工成了崭新的棉花,层层叠叠,蓬松绵软,更为惊奇的是他们在干活中竟能奏出如此动听的音乐,成为我们童年的音乐启蒙,这在那个启蒙教育十分贫瘠的年代里显得越加珍贵。
更让小孩子兴趣盎然又惊叹不已的,还是那些煽猪的人,我们那儿叫做“贼(宰)猪”。沿街叫着“贼猪——”的多是河西朱庄的,膀大腰圆者有,精瘦矮枯的也有,但都是一身使不完的力气,一个人不但能用膝盖抵住拼命挣扎的猪,还要顺手取出两颗肉球来。他骑着自行车进村,在村口喊一声“贼猪——”,最后一个字用力向下压,整个腹腔和嗓子一起用力,低沉而有力,于是一路上伴随他的叫声的,还有狗的追逐和狂吠,在村庄的上空混杂,乌云般笼罩。自行车的前面捆着一根铁条,上面擎着一条红布,这就像卖香油的木梆子一样,成为一种职业的象征,甚至连狗也知道了,所以他一进村甚至不用叫,狗们大老远就会招呼,呼朋引伴地一起对他狂吠,尽力表达一种反抗的力量。他对此不屑一顾,依然低沉地叫着“贼猪——”。很奇怪,狗或许也有自知之明,只是远远地叫,像是这个村庄一阵阵的咳嗽,直到他离开后才能治愈。
骑着自行车在村里喊着“照相唻——,谁照相不——”的,多是20岁出头的小伙子,人精神,自行车擦得也亮。选在一个亮堂宽敞的地方,把布景挂起来,像是放电影的荧幕,上面绘着颐和园,或者西湖,最前面是一个镂花的栏杆,手假装扶在上面,好像真的去过北京到过杭州一样,小孩子和年轻人就喜欢这样的布景。有时也没有什么画,就是一块白布挂在两棵树之间,一般老年人选择这个,他们知道年岁已大,照张相以备儿孙们置办后事,也给后人留下点儿念想,所以照相时不像小孩子们那样喜庆,比较严肃,又渗出一种悲凉。还有画像的,在照相没有出现之前,老年人一般是画像,坐在板凳上按照画师的安排摆出一种姿势,抬着脸一动不动。通常只画一张脸和肩膀,像现在放大的照片一样。爷爷奶奶都有一张这样的画像,但奶奶一直就不喜欢那张紧闭双唇有点儿悲苦状的画像,说画得不像,以后她也坚持不照像,所以她去世后也没有用她的画像,而是放大了她身份证上的照片。
可惜的是,这些曾经飘荡在村庄上空挤进每家每户的叫卖声,连同那些精巧的手艺,大多都已经消失或许久不见了,正如我们无忧无虑的童年一样,不经意间就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有时在喧嚣的城市路边、高楼林立的某个住宅小区,偶闻剃头刮脸的招呼声和磨剪子戗菜刀的吆喝声,总有种亲切的感觉。虽然我们的小时候越走越远了,但那些别有风味的熟悉声音一直在耳边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