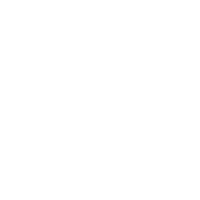【他乡寻梦】金鸣街
听到陈奕迅的《好久不见》,我的心总是不能平静,我觉得这首歌词就是写给离开肥西的我的。我想起生活过六年的金鸣街,想起我的师傅凌士彬校长,教我做课件、和我探讨教学的张道存老师,还有把我当小老弟看待的张轩老师,像父亲一样教诲我的汪家才老师,还有如兄弟般的小马和吴瑞。我知道,今生我再也回不去了。但是,我的教学生命和写作生命确实是从这里开始的。我离开后曾念了无数次的名字:金鸣街。
一
立夏一过,我搬了一次家。新居是和朋友合租的二室一厅。据说房东到省城另谋高就了,每半年才过来收租一次。屋子装潢过,看上去很舒适,也很温馨,和居家没什么两样。晴天,从六楼的阳台上清晰地望见人声鼎沸的校园篮球场,高低不齐的民居宿舍,葱茏满枝的水杉树。高远的天空有洁白的云朵,有飞翔的鸟群,颇为赏心悦目。但是八九月的季节雨水多,隔一阵子就会落下暴雨,空气漂浮着雨珠和尘埃。雨停后凉爽极了,不像太阳出来时那么闷热。
于是,我在金鸣街定居了。就从大转盘说起,因为它是整条街的纽带。这个圆形广场,中间矗立有雕刻精美的人体塑像:一个低首凝眸的白色少女高扬一只手臂,信步站立在圆形托盘之上,以一种傲然直立的气质和优雅从容的姿态呈现在我的视域中;三个翩翩少年手举酒杯分角度地驻守在下方,成为美的烘托和陪衬。我只要在远处踱步而过,即可触碰到它们在日光下灵巧的投影。草坪用栅栏围起,里面生满了齐膝的绿草,和季节一道枯荣盛衰。我曾无端地猜想,城镇规划者若在此处引一道活水,搞一个人工喷泉,不仅美化景观,不知还会添加多少盎然的情趣!两三个远道而来的生意人在北边的空地上摆有露天摊点,操着异地口音,出售四季鲜活的花,如月季、菊花、玉兰花,一盆盆一束束娇媚吐艳、婷婷而立,在初秋的时节纷纷留下曼妙的倩影,散播的素淡花香总令人心醉。事实上,我是爱花之人,但似乎从来没有赏花的闲情逸致,有的只是匆匆一瞥。不过,听说他们的花市买卖并不清淡。
更庞大的是林立其中的商贾店铺,就像豆瓣一样散落在金鸣街的巷道和里弄,随处蔓延而去,甚至将本不宽敞的街道挤得逼仄而狼狈,但总有走街穿巷的殊方游人。我曾留意过,一条约近三十米长的直巷除了居家百姓,竟容纳了布庄、理发店、麻将馆、米行、超市、精品屋,密集的程度令我有些惊叹。而那些老板和伙计,则是转盘里真正的主角,支配着此地的生活节奏,演绎着生意场的喜怒悲欢。你若留心一下,便可见不景气的店面房,正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有的店门贴上转让告示,关门大吉了,有的刚开张迎彩,人头窜进,喜气洋洋的,好不热闹,还有的店家则风风火火地开展打折活动。天气晴好,百无聊赖的店主凑齐一桌麻将,解解闷,消遣一番。牌场亦如商场,翻云覆雨,风云突变,聚散无常,时则愁眉不展,时则笑逐言开。雨天时,他们坐在柜台边嗑瓜子看电视,顾客来了,有的老板若无其事一般,不见一声招呼,顾客看到这情景自然快速地掉头离去。
有点遗憾,人烟阜盛的金鸣街竟罕见婆娑的树影,撑不开自然造化的绿意。唯有在转盘的边角种植了十棵矮小的香樟树,看上去干净整洁,加上没有恶臭的垃圾污染,还是清爽的。风也从不吝啬光顾这里。如果说白昼的风和煦,那么夜晚的风沁凉,丝丝的风语,来回游荡,拂过沉睡的或微醒的心。傍晚的夜幕下,东南角就开辟有小型的儿童游乐园。闲暇的妈妈陪着三四岁的孩子游乐,也放松心情。小孩们比较热衷此道,在画有小猫小兔小老虎图像的电动车里手舞足蹈,呼朋引伴,肆意而热闹地欢笑,就像鱼儿在活水里快意地游荡。如果天公不作美,撞上阴雨天,花市和游乐园都得快速撤离,或者用巨大的红帆布严实地盖着,待雨水一止,空气静洁润泽,顾客依然络绎不绝。
就在这儿,我见识了一种新的冷饮制品:炒冰。这两个词本来是格格不入的。冰是冷的,怎么能放在热锅里炒呢?当然,是我没见过世面,孤陋寡闻了。店柜的老板每天会把冰块和果汁之类的调料置于沙锅里,然后用大铁铲不断地搅拌,最后做成少男少女手握的一杯杯弥散着水果气味的冰块,小杯一块钱,大杯两块。今年涨价了,小杯一块五,大杯两块五。我猜想,它们只能在街头巷陌里风行,大城市里小吃花样层出不穷,谁会青睐这个呢?一个夏天以来,小镇里的顾客去去来来,生意一直很好。但这类食品却让我望而却步,更不用说想品尝了。而且,每次看到“台湾风味”的字迹就让我没由来地怀疑它的纯正性。
转盘是一个没有红绿灯的十字路口,流动着一批批隐藏着身份的陌路人。半年前,一个同事刘大为要离开这座城镇,去国外追寻更大的发展空间。我在转盘的西北角和他道别。黄昏夕阳下,清远悠扬的歌声传向我的周身,没有丝毫的杂音,空灵而飘逸,平淡而真实,可在那个特定的场合下,沧桑感和苍凉感海雨天风般积聚在我的脑际与心头,触发了作为行人的所有悲思。现代交通发达,世界越来越小,可再见的机缘却未必常有。挥挥衣袖,就回想起的王勃的诗句:“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作客。”我们没有果酒饯行,也没有慷慨壮语,我只有深深地祝愿他有个好前程。
二
回寓所要经过书摊。我戏称之为“户外书店”。两排铁桩作支架,顶上盖一块厚木板,外罩蓝色蓬布,再把铁皮围拢的长方形底座置于中间,铺面用三合板连接,书籍分列其上。整个屋棚虽小虽简陋,亦能遮风挡雨。书摊两家,两位主人各自摆弄,互为邻居,但极少打招呼有照应。我以为,多少有暗暗竞争的意思。早晨,他们把书箱放在平板车里搬运来,夜晚又照原样搬回。我始终记得西边的那个店主,一个老头子,年纪估摸在五六十岁左右,黑发里搀杂白发,脸庞瘦削,有斑纹,眼睛小而有神。老人习惯躺在靠椅上休憩,如有顾客前来,才会和你交谈,讲价。透过这个安静的角落可观察日夜流转的集镇,打量纷纷纭纭的面影,倾听细微不同的脚步声。老人却极少将视线投往远处,要么是一声不响地浏览报纸上的新闻,要么就是轻声哼唱小调,收听广播里的新闻。
我是爱书之人,也长期和书打交道,所以会在书摊前逗留片刻。文学类杂志不少,娱乐性杂志亦可数,还有厚实的散文小说集。阳光懒散的午后,我会过来淘一淘,翻翻往期杂志,可能会找到在别处难买的好书。印刷质量还行,约八九成新,摩挲着纸张,不免会勾起你想买的欲望。一问价格,打五折的,这对一些囊中羞涩的读书人还是较有吸引力的。可是,老头的书刊似乎没有出现所谓的畅销。随手翻看的多为中学生,诚心想买的更少。若遇上绵绵雨天,光线沉暗,人们似乎懒得去跟前转转,独在路过时投上匆匆一瞥。书籍可能是寂寞的,老头的生活水平估计也就维持一个温饱,也很清贫的。有一回,正逢上烈日炙热的盛夏时节,我出去办事。瞧见那老头儿安守自己的“小房子”里,躲避暑威。他左手拿一个酒瓶往玻璃杯中倒着凉爽的冰啤酒,然后举杯细口细口地饮入腹内;右手则持一双竹筷子,悠悠然夹起下酒的小菜——一碗咸豆角。我至今还忘不掉这个场景。天气难熬,生计难熬,书摊和相邻的杂货铺一样,一天下来恐怕问津的少。
近旁的小饭馆和它们仅间隔一道转弯口,可景象是截然不同。饭馆没有门牌和店名(也许有吧,但我没听说过)。外头是简易的半露天厨房,一套厨具,锅碗瓢盆,应有尽有;进去是两间屋,七八张方桌,一台彩电,不间断地播出新闻或体育比赛。老板们系墨蓝色围裙,在烟火缭绕中不停地炒饭,不时用手抓点青菜放到铁锅里。门前的马路又破,又窄,又脏,有黏稠的油状物质,又时常泼一片污水,丢弃的白色饭盒和塑料袋被风吹得满街跑。偶尔冒出几个幼嫩的小孩,疯疯地追来追去,不小心摔倒了就大声地哭泣,哇哇地喊妈妈。饭店的顾客一拨一拨地走过。要说也没什么特别的饭食:炒饭、炒面、米线和油炸蔬菜四样。大半年前,一个本地姓廖的同事曾经带我来过一趟,没料到油气腾腾的小地方竟会人满为患,等了十多分钟才空出两个座位。我们要的是牛肉炒饭,味道还行,价格不贵。以后我还来过两次,两次之后,再也没去了。
书摊斜对的是实验小学的后门。中午和傍晚散学时分,孩子们从敞开的门口蜂拥而出,铺子前,狭长的过道里,大人和小孩碰挤着行走,簇成一股股浩荡的人流,也聚合了浓浓的人气。临时摆上的麻辣串、小吃铺倒是热闹得很,围上一群欢愉的小学生。沿着它的近旁,有走卒贩夫,有引车卖浆者。把目光朝远,则看到密匝匝的黑瓦房,它们和灯火辉煌的门市部在暮霭中交融,分不清哪是住宅区哪是商业街了。
吴老板是我认识的一个朋友。五十开外的年纪,络腮胡,圆方脸,和老伴在书摊边摆麻辣串。下晚4点左右他骑上三轮车过来,深夜10点钟收摊回家,而小学放学和晚饭时间是吴师傅生意的高峰。他做活熟练,动作麻利,即便是顾客蜂拥而至,他也绝不会乱了阵脚,各人要哪几样,付多少钱,他都盘算得清清楚楚,丝毫不差。我常看他一边把搁在玻璃板的硬币捋进盒子里,一边把顾客点的年糕、海带、里脊肉等一并放到油锅里。若遇到五十、百元大钞,他会谨慎地拿起,对着日光或电灯光瞅瞅,才放心地给别人找钱。
香喷喷的油炸小吃在天生爱吃零食的小丫头眼里怎么也不会过时。小姑娘常常隔三差五来此消费,且将它们当做晚餐的主食,在旁边的小圆椅上坐定,吃完一碟又要一碟,花钱阔绰,吴师傅总是乐呵呵地为她们忙碌着,还不忘善意地提醒她们,说这东西既不能减肥,也不能美容,回家多吃米饭才养身体。小姑娘们只管大吃大嚼,满嘴是油,顾不得那么多了,礼貌性地点点头,也不知听进去没有。我每次来都喊他“老板”或“师傅”,他见我也客客气气的,喊我“小老师”,我要3块钱的鸡柳他给的分量比别人稍多一点;偶尔我来迟了,排在人堆后面,他发现是我,忙对别人说:老师先来!就把我吃的优先放到锅里,我一下子被亲切的气氛包围,脸也唰地红了。我们混熟了,他以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口吻说,今后打算把小孙子送到你们学校念书啦,老伴听完插进来一句话:孙子读高中还不知要等到哪一年哦。现在想想,老两口子还真得味。有闲功夫,老吴指缝里夹一根过滤嘴香烟,跟隔壁三个生意贩子打纸牌消磨时间,输赢不过20块钱,谁也不计较,就图个“乐”字。遇到好玩的事,老吴总是第一个哈哈大笑了。我上晚自习回来,碰见他正收拾着要打道回府,我肚子有些饿,遂上前问能不能炸两串腐竹,他没犹豫,拧开液化气灶,不出一分钟,从油锅里出来,用饭盒装好,递给我,一吃,热乎乎的。其实,摆小摊赚的每一分钱,包含着劳累的付出。
继续朝西行,可抵达街口,除了路标、石墩,就是几棵矮小的棕闾树。左侧楼顶,高挂一则广告语:老明光,穿透岁月的味道。实际上,我已闻足了一条街的酒气。濡湿的,潮润的,甜腥的,咸涩的,五味杂陈。当我走出金鸣街,便走进了通衢大道——巢湖中路。我曾数次见到卖冰糖葫芦、卖甘蔗、卖糕点的小贩子们,他们的面孔一一掠过我的视线。另有几个摩的司机,他们摆着固定的坐姿,目光四处漂移,也不主动吆喝,耐心而又无聊地等候着那些需要搭载的顾客,花上几块钱,他们可以将你快速送至县城的任意一个街市和拐角。沿巢湖路一直向北,可通往合肥,通往全省,通往更广阔的天地。金鸣街就被搁置于身后,淹没在无声的潮流里。
数年之后再来回看金鸣街,我觉得自己在那里做了一场梦。梦里,我的世界很小很小,仅仅就是一条街的生活空间。梦里,晨光熹微,我携带着几本书去学校看早读,偶尔遇见几个同事,顺便打个招呼。梦里,我看到许多学生骑着车子形色匆匆,而一辆30路公交车从街口开过,我抬头,它已经去了远处,留给我一个模糊的背影。我想到杜甫的两句诗:“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明天,我还在这里吗?